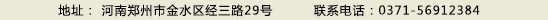胭脂红唇
胭脂红唇
文
糖豆
一我高一那年的寒假,去了哥哥所在的Z市。
把我当命疼的哥哥用一台拉风的摩托车带我游荡在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吃喝玩乐。身为武警的哥哥练就非常敏锐的视觉听觉,他喜欢用敏锐的视力发掘视野里的每一个美女,尤其是细腰、唇色自然胭脂红的美女。
他是个那么痴情又那么滥情的人。
他跟一个有着胭脂色红唇的女孩相恋了五年,分手了。
他又找了一个,两个,三个,后来我也数不清有多少个。只知道,他的女朋友,他的胭脂红唇们,按季节甚至月份变换着。而我与哥哥的胭脂红唇们的缘分,有时只限于吃一次饭,唱一次歌,或喝一杯奶茶,下次看见的或许就不是同一个了。
胭脂红唇们都把我当小妹客客气气地疼爱着,又真真切切地嫉妒着。
哥哥处得稍微久的胭脂红唇,我接触得多的,也就熟悉了。我穿她们的高跟鞋,系她们镶水晶的皮带,拂她们的风铃,睡她们的床,喝她们的栗子粥。
哥哥的车后,不停地变换着女孩子,只有一个是不会变的,那就是我。
那晚KTV散场后,哥哥骑车带着我,街市拥堵,他便拐进一条小巷。
小巷里弥漫着暧昧的脂粉气,一群女人妆容艳丽,大冷天,却穿着长靴丝袜短裙,露着小半个胸脯。远远近近的LED灯霓虹灯明明暗暗,在她们浓得夸张的妆容上闪动。她们妩媚而梦幻,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哥哥。
在这个不算太繁华的城市,如此妖娆的妆容实在少见。
我说,cool!
其实跟cool没有关系,我只是想表达我的惊讶。
哥哥说,她们是站街女。
虽然是第一次见这种女子,第一次听见这个词,我却瞬间明白了。
站街女。
二我上大学了,从南方水乡去了遥远的首都北京。
暑假,当我再回到Z市时,哥哥的胭脂红唇又换新了,他一如既往地郑重介绍:我妹妹。
他从不介绍胭脂红唇。胭脂红唇迟早会像唇蜜被擦去一样被舍去的,我也不打算认识。
我已经能开着哥哥的摩托车横穿城市,他不管我。
在那丛霓虹灯下,美丽的女子仍然美丽。
她们的眼睛勾过来,无声说着渴望。
男装车上男士头盔黑色运动装的我,心尖上有一千只虫子在爬动。
我一拧油门飞驰而去。
三胭脂红唇说,小妹,鞋柜里有双新的高跟鞋,你穿去。
她没有问我去哪里。
只有我自己知道这双12厘米的高跟鞋会带我去哪里。
时间才九点,这个城市的夜生活,刚刚开始。
不远处的广场,传出鬼哭狼嚎的破锣嗓歌声,那质量粗劣的音响,把破音放大,震天地轰炸过来。这就是南方城市的特色了,把音响麦克风搬到广场,广场就变成了一个大型开放的KTV,要唱歌,2块钱一首,管你是谁。于是各种歇斯底里的嗓子唱着跑调的歌,把夜色煮沸。
我踩着高跟鞋走进小巷。灯明灯灭处,浓妆艳抹的女人倚墙而立,静待生意上门。
“我买的蕾丝内衣到了,哈哈你知道吗送快递那个男的看见单子上写的情趣内衣,脸都红了。”一个女人笑得花枝乱颤。
“不该啊,店家一般很注意保护隐私,不会瞎写单子上。”另一个女人说。
“哈哈哈,写了好啊。那送快递的,我轻而易举就做了他的生意,你不知道······”
见我走近,对话戛然而止。
我选了一个较暗的墙角立住。女人们拿眼角余光偷偷打量我。
偶尔晃过几个男人,有意无意张望,在附近踱来踱去,眉眼里尽是暧昧。
夜像水蛇一样滑动、流淌,我身边的站街女一个个少了。
她们多是被那些穿着灰色工衣或浑身泥浆的男人带走的。
当他们一前一后默契地向小巷更深处走去的时候,我甚至能闻到女人身上淡淡的香水和男人身上浑浊的汗味。
很奇怪,竟然还有开着车来的。很难想象他们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开得起私家车却找最低等的小姐——站街女。
他们摇下车窗,对某一个或几个女人勾勾食指。女人便消失在关上的车门。
我站了3个小时。那个做了快递哥生意的女人,来到我面前跟我说,你的妆太素,裙子可以再短一点。
我看着她。她丰实的胸,要撑开低胸装弹出来似的。眼线飞出眼角,甚是狐媚。见我不搭理,她自顾哈哈笑着,说,这儿的姐妹都叫我桐姐。原来没见过你,你是哪里人?几岁了?
我依然不说话,她终于不再来自讨没趣。
如是两晚,我的裙子依然长,妆依然素。高跟鞋也索性不再穿。守着自己的地方,每晚看着女人们光溜溜的双肩和听着嗒嗒的高跟鞋声远去。
第三天晚上,一双球鞋和一缕烟停在我面前。
我自小对烟味敏感,芙蓉王的味道并不陌生。这缕芙蓉王引着我,在黑暗的小巷穿行。
目的地是一个,网吧。
芙蓉王开了两个电脑,他没有说什么,打dota的人,能有什么话。我从不喜欢猜测别人葫芦里的药,想起李编辑推荐给我的《美好的一天》还没有看,网吧的电脑效果好,正好可以看。
美好的一天不美好,我趴在电脑前睡着了。芙蓉王拍醒我的时候,已经凌晨一点。
他取了一张钱给我,我接了。他说,我只是想知道女人陪在身边打游戏的感觉。我说,我只是想知道站街的感觉。他说,站街女不会看《美好的一天》,你看了,所以你不是。
我看着他的球鞋,说,打dota的人,怎么会关心有没有人陪。只怕你是有陪你的人,那个人根本不让你打游戏。
我有军人情结,这个男人,即便他不说,我也知道他是部队出身的。部队训练出来的骨骼,不会撒谎。
四这片临着第三工业区的暗巷,站街的女子多的时候有二十七八个,少的时候只有十来个,她们有自己划定的区域。站街女的年龄集中在三十到五十之间,她们大多是从流水车间走出来的。这个职业,年龄与收入成反比,四十岁以上的女人,主要客人是工厂男工、建筑工人,价钱在一百左右,年龄大又没有点姿色的,几十块也愿意。他们不花钱住宾馆,由女人带回出租屋。
在这些站街女中,有一个女人与众不同。从桐姐和其他女人的口中,我知道她叫Shmily,但是大家更喜欢喊她——睡美丽。
睡美丽是霓虹灯下最艳丽的色彩,她身材高挑,曲线傲人,脸蛋美艳,是那种逼人的美艳。再加上年轻,她的价钱不比一般夜总会小姐低。
谁也说不清楚为什么睡美丽条件这么好,却不愿意进高级会所,偏要抛头露面站街。
我喜欢看睡美丽红色恨天高上修长的双腿,网状丝袜诱惑着过往男人贪婪的眼。睡美丽的眼却盯着我,她说,你要懂得规矩,姐姐划出的圈子,不要踩,一脚都不要。
我真喜欢她那种跋扈的样子。
她的唇彩红得烈焰一般,不同于哥哥的胭脂红唇。
一辆面包车开过来,睡美丽摇着肥臀走上去,趴在车窗娇笑连连,我看到车窗里伸出一只手,在她胸前抓了一把。睡美丽谄媚夸张地笑着。
这时来了一辆黑色比亚迪,斜倚在路灯下的女人,坐在板凳上的女人,瞬间调整好了姿势,更加妩媚,更加,放荡。
睡美丽立刻丢下面包车。面包车丢出恶狠狠的一句:妈的!婊子!
比亚迪带走了睡美丽。
这一晚后,睡美丽好几天没出现过。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也没有人关心为什么。站街女们只知道,少了一个竞争对手,是好事。
五就是比亚迪带走睡美丽的那一晚,一辆山地自行车也带走了我。
那是一个十七八岁大的男孩,也许只是个高中生,挑来挑去,也只有我最年轻。他的肌肉紧致,皮肤黝黑,像是篮球打多了晒出来的。
男孩轻车熟路,花几十块钱在小破街里开了个钟点房。
我站在门口,房间里有一张床,白色的床单洗成黄色,像是被陈年的蚊子血染过,再也洗不干净。我茫然了,不知所措。男孩问,“你先洗还是我先洗?”白色的牙齿与黑色的皮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那一刻,我沉睡了一百年的心脏扭着身子要苏醒了。
在我的低腰裤袋里,一直备有一只durex,这是我在超市收银台看到时随手抓下的。但是我希望我永远用不上它。
我说,你先洗。
哗哗的水声传来,我心跳得厉害。
浴室的门竟是开着的。我摸了摸裤袋,走近浴室,透过度隐形镜片,透过迷蒙水汽,当我生平第一次看见一具全裸的男体时,我受到了很大的惊吓。
我逃跑了。
睡美丽回来了,坐在铺了餐巾纸的墙角,没有穿高跟鞋,只有唇色依然红艳得像要滴血。我说,你来了。
睡美丽吸了口气,淡淡回了个嗯字。没有高跟鞋的她,不再如往日盛气凌人。
“你不见了很多天······”我斟酌着该不该问,担心惹毛她。
“遇到变态了,”睡美丽顿了顿,看看周围,女人们离得远,没有人注意我们,眼前也不像有客人要来的样子,她压着声音咬牙切齿地说:“遇到变态了,就那晚,那老男人带我去了酒店,我才知道不只他一个,还有两个已经等在那儿了······”
“我要走,可他们开出了一万的价格,我一算,一万块,得在这儿站多少晚啊,就答应了。我没想到他们那么变态,带着整整一箱的情趣用具······”
“不怕你笑话,那晚我以为我要废掉了······”
“我休息的那几天想清楚了,这一行不能久干,我一直有个开花店的愿望,等我赚够了本钱,就不干了。”
长久的沉默,广场传来的歌声尖锐刺耳,一个女声在唱:天不刮风天不下雨天上有太阳,妹不开口妹不说话妹心怎么想。
睡美丽摸出一支烟点上,吐着烟圈问,你呢?没有人找?我跟你说,你要做这行,不能这样冷。你看你这素的,谁要吃你这样的清汤挂面!
我第一次去了睡美丽的住处,一个一厅一卧的房子,不像一般站街女的住所。睡美丽打开衣橱,说,你自己挑一件。她给我扑粉、上妆,说她的过往,无非是上学,谈恋爱,辍学,出来工作,重新谈恋爱。
风从开着小半的窗口溜进来,窗帘拂动,风铃碎玉般清脆的声音响起,我抬头,是个螺旋式的风铃。
六芙蓉王偶尔来找我,有时去网吧,有时去电影院,有时去KTV唱歌。他固定给我一百块,用这些钱我买了几十本杂志,对着栏目风格写稿,投稿。
哥哥回了老家,胭脂红唇上班,没有人管我。黑夜里的我是个浮在睡莲里不知激流的拇指姑娘,我用玩世不恭的心偷浮生一把乐。
这个平稳的人生,需要一些疯狂的事情去调剂。在体验疯狂的时刻,我的内心依然希望能够把握自己,掌控事态发展。比如这哥哥知道了非气死不可的站街女体验。
芙蓉王来找我越来越频繁了,并且不仅限于晚上。他看我的眼神一日不同一日,也不再给我钱。我开始躲着他。
我一直没有接别的客人,站街女们早就对我产生了怀疑,她们私下里议论我是记者,是女警,都躲着我,但是这么久的毫无动静,她们又放松了警惕。
桐姐和七珠却开始努力对我示好,希望我能把不要的客人给她们。
七珠是桐姐的老乡,二十多岁的样子,实际年龄只有十九岁。她技校念不下去,就出来了。念书时谈了个小混混男朋友,谈了不到一年,小混混找了个比她漂亮的,就不要她了,她的名声却臭了。
七珠家境不好,但也没差到要她做这个职业。走这条路,只不过是没有一技之长,也没有吃苦耐劳的毅力。睡美丽不喜欢她们,叫我不要理,但是桐姐是个可怜人,我想帮她。
桐姐三十出头,虽不算特别漂亮,但据她说,结婚前也是老家有名的美人。她书读到初中,妈妈肝硬化去世,弟弟妹妹还小,她辍学回家,不久嫁给大她十岁的代课老师。原本过的也是普通人家的幸福日子,不想丈夫在一次晚自习下课后骑摩托回家出了事,把命丢在半路上。
她当时已经有一个两岁的女儿,又有了三个月的身孕,婆婆坚持要她生下来。小孩生下来不到一岁,她就离开家来了Z市,原来在电子厂里当了几年女工,但是丈夫的保险赔偿金花完后,她的收入根本不够孩子的生活费和弟弟妹妹的学费。她只好辞了工作,铤而走险,做起站街女。
这些年,她进过警察局,罚过钱,也被人欺骗过,血本无归。
桐姐说这些的时候,脸上很平静,生命给她的一切她都受下了。我问桐姐为什么不找个人嫁了,她说,再等等,多赚几年钱,弟弟妹妹毕业,父亲有人照顾,我就带着女儿改嫁,儿子是婆婆的命根子,不会让我带走。
原来,每个人都是有故事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难。只有我这样没有故事的人才会无聊到要通过站街来体验生活。
七那晚芙蓉王来找我时,一个醉酒的秃顶男人正把数好的6张钱举到我胸前,他一定想把钱塞到我的胸上,可惜,我穿的是有衣领的雪纺衫。
我要是知道这个价吓不退他,我会翻一番这个数字,说,块,先生,先付钱。可是,我已经没有反悔的机会了。
我顺从地上了他的奥迪。
当我回来时,七珠不在,桐姐面部表情很丰富,说,你真行,,都比睡美丽高了。
这时我看到了愤怒的芙蓉王,他瞪圆的眼睛要喷出火来。桐姐说,那人一直没走!
芙蓉王把我拖到一个黑暗的角落,堵在墙上,他扬起了拳头,我本能地闭上眼睛,却听见他一拳砸在墙壁上。我反应过来,怒不可遏,一巴掌扇在他脸上。他忽然就摁住我的后脑勺,狠狠地吻了上来。他像一头暴怒的野兽,一只手放在我的腰上,手指像铁钳一样,一直在用力,仿佛要钳碎我。
我突然就有了一种自暴自弃的感觉,我想,来吧,有本事就把我捏碎!
疼痛,伴随着一种醉醺醺的感觉,在我的大脑神经里肆虐。我的脚发软,眼睛睁不开。他的手伸进我的雪纺里,从我的腰到肚子,像爬虫一样往上爬,爬到我最敏感的地方停住。
去他妈的伦理道德,去他妈的婚姻爱情,这一刻,哪管天塌地陷,让我疯狂一次,就一次,就一次!
当我的思维又能正常运转时,我看到芙蓉王在盯着床上的一抹红色。像被冰块砸过,他寒着脸问我,这是怎么回事!即使你以前没有过,可是刚才,那秃顶老头,明明给了你一叠钱,我亲眼看到他把你带走了!
我环顾这个从始至终没有好好看清楚的酒店,我记得我闭上眼睛任由他的一只手在我身上游走时,他打电话,说订房间,说会员卡。
芙蓉王当然不知道,那个被他夸张为老头的秃顶男人,把我带到酒店后,接了个电话就跑了。
哥哥的朋友圈,包括刑侦武警特警交警辅警,我跟哥哥混多了,他的许多朋友我也熟,拜托扫黄组放个风还不简单么。
八支付宝里接到了暑假的第一笔稿费,我就揣着银行卡去“云想衣裳”旗舰店看裙子。
很意外地,我看到了芙蓉王——西装革履的芙蓉王。他从宝马车下来,被一个肥胖的女人挽着胳膊。女人的脸上画着精致的妆,却丝毫掩盖不住半老的容颜。布料上乘的衣裙,裹着肥胖得像要挤出油脂的腰身。
芙蓉王也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眼里的忧伤。他的眼神是那么的无辜和受伤,就像夕阳下被割了喉咙的绵羊,说不出的悲凉。我听见自己心碎成血渣的声音,那种颜色,跟那晚白色床单上染出的花朵一模一样。
那个富态的女人,礼貌地对我微笑。
九当秃顶男人又来找我时,我把块钱还给了他,他说,我加钱。我喊来七珠,七珠拿了块,跟着他走了。
哥哥回来了。他包了一个钓虾场,请了朋友钓虾,烧烤。
如果我知道我会在钓虾场看到芙蓉王,我一定不会去。
哥哥给我介绍他的朋友,他不说这是某某单位某某职务某某人,他说这是某哥,那是某哥。到芙蓉王时,哥哥说,叫华哥,他是当年睡我下铺的战友,关系铁着呢。他上半年才来这里,所以你没见过。
芙蓉王认出是我,脸抽了一下。我的心火烧火燎地揪疼起来。
哥哥很得意,一拳打在芙蓉王肩膀上,说:我妹妹漂亮吧?不过我可告诉你,别打她主意,还在北京上大学呢!
十我没有再去小暗巷。白天安心看杂志写文章,夜里早早睡去。表面的风平浪静,背地里的波涛汹涌。我很明白,也许哪一天事情捅出来,哥哥会跟芙蓉王打一架。而我是不能做展颜的,当季冬阳跟方以安打起架来时,她坐在旁边安安静静地吃蛋糕。
稿费一笔一笔地来了,也不多,但是足够我买一些轻奢的裙子和口红。
我还没买呢,夜里就听到胭脂红唇跟哥哥吵架,吵得很凶,原来她看到哥哥的手机,一个女人发来的信息:我怀孕了,你看着办吧。
我于是买了一双8厘米的高跟鞋送给她。
有一天路过睡美丽的住处,我买了个西瓜去敲她的门。睡美丽看到我很惊讶,问我怎么突然消失了,还以为不小心被抓进去了。
我第一次看见她卸了妆的样子,眉毛弯弯的,唇红如胭,脸白如脂。没想到她素颜也这么美。
睡美丽高兴地跟我说,她准备不敢干了,她一直想开个花店,现在正好有个机会。
我问她钱够么,她说,你要借钱给我么?钱就不用了,你给我的店想个名字吧。
我说,那就叫睡美人花店吧。
(十一)
再见芙蓉王时,他像是老了许多。
他看我的眼神里,多了一些复杂的东西,是愧疚?是悔恨?是无奈?我说不清楚。
芙蓉王是一头外表的狼,内心的羊,我早就知道的。这一刻,他是温顺的羊,就跟他在那个富女人身边一样。他对不起他的战友,他的兄弟,因为他睡了他的妹妹,他心里有愧。
我想起那个夜晚,在那个灯光暧昧的房间,他的眼神迷离,他的嘴唇从我的耳根滑到我的脖子,在我的脖子上啃啮。我说,你真像狼。他吐字不清地说,你是我最鲜美的猎物。
狼喜欢猎物鲜美的血肉,他说我是他最鲜美的猎物。
可是,当我躺在他因严格的体能训练而变得粗壮的臂弯时,他不是狼,他的心里有一只温柔的羊,羊低着头在夕阳下吃着青青河边草。
可是我喜欢狼。带羊性的狼,是驾驭不了我的。
我用我锋利的一口白牙,咬在他的手臂上,直到我的舌头尝到了腥甜味。
我只是想知道,芙蓉王除了芙蓉王的味道,还有没有别的味道。我只是想知道,芙蓉王的血液里,是不是也有芙蓉王的味道。
(十二)
吃早饭的时候,早间新闻报道,“女富商欲挽回变心情人,反失手将其误杀”,我抬起头,看见那双熟悉的球鞋,还有那个富态的女人,对着镜头泪流满面。
我离开了Z市,回到北京。
我穿长裙、梳长发,每天怀抱书本,上课、下课,检查支付宝上新的入账,当我的女大学生,听外院的男孩在背后喊女神,仿佛从来没有过站街女的故事。
哥哥换了新的胭脂红唇。听说新女朋友非常漂亮,有个性,有想法,会赚钱。哥哥喜欢她喜欢得不得了,那么花心的人,竟也收心了,甚至动了结婚的念头。
“你个花心大萝卜竟然要结婚?你女朋友到底是有多漂亮啊,竟能降住你!我就不信了,难道是仙女下凡?”
“给你看看照片就知道了。”
我点开哥哥发来的照片,睡美丽坐在花房里笑靥如花。
辣条走起
赞赏
人赞赏
北京中科医院坑白殿疯症状初期图片转载请注明:http://www.dongyamedia.com/yzcf/947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