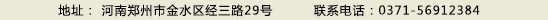美文殿堂不问胭脂借淡红天真无邪
文
——
不问胭脂借淡红
文/天真无邪
(图片源自网络)
我低下头,用仅可以两人听到的声音低低地开口,低低地对着他道:“你会死的,你和她都会死,在我偿还给你们的痛苦里,一点一点地死去。”
本文刊载于《飞·魔幻》杂志.5A
第一次见到董少卿是在洞房夜,喜娘喜滋滋地对我说恭喜,讲董公子如何才华横溢入得我身任知府的父亲眼中,从此一举夺魁,入赘沈家做了我丈夫。
有赧色浮上我脸颊,却难以不从心底衍生出一丝喜悦。在洞房的花烛下,他身着赤色华服缓步朝我进来,带着恍惚的笑意,似乎有些不开心。
喜娘略带歉意朝我解释:“姑爷喝多了酒,大约有些醉。”
我将他扶到床上,待众人行礼退去后,替他解开上衣繁复的衣扣,手移至他胸口处被他灼热的手掌猛然覆住,我下意识便要挣脱,而他另一只手略微抬高,轻柔搂上我脖颈,稍稍用力便将我拉到他胸口处,耳廓擦过他温热的唇瓣,正听清深醉中他喃喃说出的一个名字:“桑若。”
我愣了愣,呆呆地伏在他胸口出神,也在心底低低念:“桑叶未落,其叶沃若。”有这样好听名字的姑娘,定是才情出众,而被这样一个男子记在心底的女子,她一定很幸福。
一:
董少卿待我,不可谓不好。
闺中画眉,赌书泼酒,琴瑟和弦这些事他虽从未放在心上,但我并不为意。他是一个大丈夫,理当以天下苍生为命,如何能痴缠于这些许儿女情长之上,是以他在新婚第二日提出,以科举进考之名,要求自此之后独睡书房的请求时,我愣了愣,却也并无太多犹豫便应许了。
董少卿像是松了极大一口气般,温和地朝我一笑,微有窃喜。虽深知无法直达他心底,纵然卑微如蜗牛般靠近,我也甘之如饴。
父亲很快察觉我和少卿的分居,怅然叹:“菀菀,我不知道这自作主张的婚事有否让你如意,我只希望你能得到幸福。”
我笑得仓促,告诉父亲,也当是告诉自己:“我的丈夫需才华当世,文韬武略,无一不是英雄,少卿便是菀菀心中所想,并无其二。”
英雄的心是这样小,一分为二,一半是天下,一半是红颜。只是红颜之下,却并无我沈菀的位置。
我这一生,只求他能将我看进眼里。
第二年春天少卿三元及第,受六品翰林院修撰,政务也比先前更为繁忙。将少卿从书房移置回新房的建议便自此搁置。
有时候夜深路过书房,若是见灯亮着,我必会命侍女送些进补的汤水。一日侍女来回禀说敲门许久未见姑爷来开门,觉得不安便请我去看看。
我并未多想,自行推门进去后发现他伏案深睡,两颊呈现醉态时才有的晕红,竟是独自喝了一夜的酒。
我搁下托盘,欲将他从书案上扶起,行动间不意有纸张自他肘下落到地面。俯身拾起,横竖遍布的只有两个字:
桑若。
稍许声响将他自深睡中惊醒,他一手撑住桌面,一手轻柔眉心,轻轻开口:“桑若……”
我不说话,静静将羹汤呈递至他面前,淡道:“将这个喝了,解解乏吧。”
他并未当即饮下,有些歉意地低声开口:“菀菀,我想,将桑若接到府中……”
跳跃的灯火炸裂于彼时相视无言的氛围中,将他拖曳于灰色墙壁上的阴影重又染上一层暗色痕迹。
我愣了愣。
那是我的丈夫,心中念念不忘别人的丈夫。
他以为我是拒绝的沉默,急急起身,行动间带倒我搁在他手边新进的一碗羹汤。
这汤在火上熬了数个时辰,我恐火旺失却鲜味,便索性一步不错跟在炉子前。
少卿喝了这一年,却从未有问过一句。
他伸手握住我上臂,情急之下失了力道,我吃痛略后退两步,抬头却撞进他深沉炽热的双眸里:“菀菀,我知道是我不对,但是你不知道我和桑若……我和她……”
有股灼热自心底泛起,我努力睁大眼睛,不让眼中水汽凝结成水滴:“那,就接回来吧。”
少卿展眉,笑意自嘴边延展直至点燃眸心那点光亮,他就这么看着我,熠熠生辉到让人绝望。
二:
见到桑若,我才略微理解他的念念不忘,那女子温婉如枝头花朵,楚楚可怜。我勉力朝她笑了笑,命人领她去自己的房间。
不料就是刚刚转身的工夫,她甫然跪下,膝行数步直到我面前:“沈小姐,求求您了,求您让我和少卿哥哥在一起吧……”
我被吓了一大跳,下意识地提着裙子后退数步,她两手原本扯着我裙子下摆,因我这一退便没有跪稳当。
行动间一人自左前方狠狠将我往后一退,动作迅疾。我扶着侍女的手勉强站稳,看见的正是一身玄色衣裳的少卿俯身将桑若自地上抱起,垂下处事不惊的眸子细细看我。
那眼神让人发冷。
他举袖拭去怀中女子鬓边无意沾染的飞絮,若无其事道:“桑若身体不好,还请夫人莫要为难她。”
我稍稍退后两步,觉得痛,痛得喘不过气来。那种痛又不像小时候磕到手,过些日子便自然痊愈,更像是有人用针密密扎在心口,苦不可言,苦不堪言。
服侍我的侍女实在气不过,走上几步想要理论。少卿垂目静听,须臾便抬起头来看我:“菀菀,桑若无辜……”他蹙眉,想必在寻找更加易我接受的词语,“如果你真的无法容下桑若,我会和知府大人禀明,你我……”
我怔了怔,用此生尽可能无瑕的笑容迎视少卿,以及他怀中女子略带挑衅的目光:“沈菀只知道从一而终,你从前成我夫君,我若无七出之错,便断无离合之意。”
有时候强硬可以保护别人,而更多的时候,强硬伤害到的,还是自己。我目送少卿抱着桑若慢慢往回走,目送他们逶迤于地的身影徐徐重叠,觉得自己这辈子,也就是这样了。
自此之后他来我房中的次数越发之少,因储相的身份,父亲亦很难与之置喙。
直到传出桑若有孕的消息。
她是上个月初来沈府,而府中大夫诊出的,却是三月有余的身孕。彼时正是科举殿试之前,他曾以学业烦扰为由,提出独住书房。
我慢慢抚上心口,却也感受不到任何疼痛。爱情之百折不回,并只是依靠一个人的力量可以抵达,而这些年我做的,也不过是妄图以自己单薄的力量,披荆斩棘,抵达他心底罢了。
我去书房找他,到门口即被告知不在房中。
愣了愣,转身却见他气冲冲朝我疾步而来。
眉目是我见惯了的儒雅温和,混杂着目中难以抑制的悲愤。他突然发力狠狠地捏住我手腕,将端在右手上的汤药直直递到我面前,冷道:“这是你送到桑若房中的吗?”他咬着牙,“沈菀,你真狠,我怎么就没看出来,你有这样一副阴毒的心肠!”
桑若饮了我送来的汤药之后,便有小产征兆,经大夫才勉强保得腹内胎儿。就在那碗药里,被验出竟多加了一味藏红花。
我觉得无力,一点点滑坐回廊冰冷的石阶上。垂首看地面上那茕茕孑立的孤影,这样寂寞,一生的寂寞也抵不过那一刻冰凉。
“那就离合吧,我同父亲说。”
少卿将手中那副汤药就势一摔,瞬时碎裂。锋利的笑容趁着艳阳,他冷冷开口:“好。”便愤然摔袖离去。
然状元之妻,于少卿身任储相伊始便已封了国夫人,离合哪有那样简单,这样一番意气之争便被延滞,直到一年之后的一场政变。
文渊阁一微不足道的文臣以“矫正枉法,循笃私情”为由,参了董少卿一章,此后便有台谏纷纷网织各种罪名参告当朝状元郎。最苦的便是他刚刚出仕,并无强大到足够的人脉来保他周全。
今上微服私访来沈家的时候,我隐隐便察觉,有一场更大的惊涛骇浪等在其后。
沈家众人及桑若躬身跪在门口迎候,我深深低着头,能感知的也只是自身边而过的一道凉风,行经我身边时有暂时的停顿:“沈菀?”
我恭敬回禀:“正是臣女。”
下巴被什么冰凉的物什挑起,迫得我移目往上看去,堪堪对准的,恰是一双斜飞入鬓的眸子:“都说沈家女儿长得俊,朕今日一看,却要比这俊还要灵上几分。”目光微不可察地扫过身侧,董少卿伏地跪在我身前,平静到无懈可击。
幸得父亲自边上讪笑着,插进来一句将话题引到别出去。我举袖拭干额上汗水,轻轻松了一口气。
自此今上也在沈家住了下来,日夜定省便也难免,也不知是我有否多心,但凡有今上在的场合,总有猎奇的目光逡巡于我身侧,让我每次在面对他都有一种濒临悬崖的恐惧。
而今上所做也不过是悠悠注视我,注视我坐立难安的神情,笑得有如目的达成般窃喜:“你似乎很怕朕?”
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句子来解释,坐我上首的少卿挡在我之前缓缓站起,和颜替我作答:“内子只是感慕陛下威仪,有些失态罢了。”
我略带讶异侧首看他,却到底无法遏制自心底而起的暖意。
我想,他或许也曾在乎过我,即便只是一瞬。
三:
是夜,我因受此惊吓找了些许风寒。少卿命人熬了一碗药送到我房间,我不疑有他,当即喝完。其后便跌入沉睡,等到我被身上灼热惊醒时发现,我竟在今上的房内。
入目所见被添上一层旖旎的景象,身体似正处于煎熬之中,夹杂着火山和冰海,喧叫着亟待释放的缺口。
我隐约有些想明白,却又恍惚,身上的滚烫却不给我足够思考的时间,房门被人从外面推开,今上含笑朝我所在的方向缓步走来。
这辈子,有没有恨过什么人,此刻我却恨得连头发丝都在抽痛,恨不得提刀杀了自己。
今上笑着拨开伏在我面上的凌乱发丝,凝睇着我略有些恍惚:“朕以为你对朕存有偏见,直到刚才,朕才知道你的身不由己……菀菀……”他温热的唇吻上我的眼睫,一点点吻去上面冰冷的泪珠,喃喃道,“不要怕,菀菀,即便是为了你,朕也会放过董大人……”
我僵了僵,挣扎于心底的最后抵抗在他说出董大人和沈家时终于瓦解,乃至崩溃……仰面自蒙眬的泪眼中看去,雨后天青的帘帐在逐渐流失的意识之中丧失最后的色彩,直至轰然碎裂。
我这辈子,再也没这样爱过一个人;这辈子,我再也没这样恨过一个人。
翌日,今上先行梳洗去了外室,我躺在床上只当做不知道,他又好气又好笑,连连摇头且叹气:“这么大了还像个孩子,看你今后还要不要见人。”
我侧脸向内,漠然不发一词,今上只当我是不好意思,待他离去之后,我命人将桑若请到我房内。
六月盛夏的阳光自窗外漏进来,可以想象层林尽染,入夜应当有疏月朗照。我漫不经心自妆奁盒内挑了一支尖端锋利的银簪,心里却在想,为什么他们可以这么快活,可以这样毫无负罪地活下去?
桑若来见我的时候已经显怀,双手覆住腹部,神色不安地朝我施礼。我示意她坐得离我近一点。她惊惧盯着我,一时不敢靠近,我缓缓站起来,指尖轻点上她腹部,低声在她耳边道:“多么好的时机,今上在花厅面见董少卿和我父亲,有些事,你和董少卿欠我的,便在这里神不知鬼不觉地,还了吧。”
她惶恐地仰首看我,我轻笑着抬高握着银簪的手,落点是她左颊上方,旋即飞快下滑,在一阵短促尖锐的惊叫声中,我淡淡引袖收手,有血珠急促地自尖端滚下,伴随桑若歇斯底里的尖叫。
叫声引得今上破门而入。董少卿跟在其后,他疾步上前抱起桑若,仿佛我们最初相见的时候,他抱起设计跌落于地面的娇弱女子,将一切怨怼遗之于我,而我毫无能力,亦没有人愿意听我解释。
但是,自今日起,实在不是一样。
今上面带不忍,瞥一眼桑若尽毁的侧脸,却也不忍苛责我:“好端端的,你又是发什么脾气?”
我微微一笑,将所有年少的不甘、愤怒,和绝望融入那再简单不过的一句话里,而此后,我就不再是沈菀了,那个沈菀死在昨夜,被他的丈夫和丈夫的妾逼死在那个没月亮的夜晚。
“失手。”
董少卿抓住那两个字,冷冷地看我:“只是失手?”
我笑了笑,用手帕拭干其上分附的血珠,漫声应道:“是啊。”
在他抱着桑若离开之前,我低下头,用仅可以两人听到的声音低低地开口,低低地对着他道:“你会死的,你和她都会死,在我偿还给你们的痛苦里,一点一点地死去。”
行走在空气里的背影便僵了僵,他抱着桑若,在赤色阳光中侧过头,看了我最后一眼。
四:
父亲是个很好的人,也极其耿介。我委身于今上的屈辱我可以咽下,但是并不代表我的父亲能和我一样隐忍。我能想象的便是他得知我被自己丈夫为仕途安稳送到皇帝枕边时,他宁可沈家就此满门抄斩,也不会让这样窝囊地活下去。
我不知该如何同父亲讲,他似乎还是在府中异样的氛围中察觉到什么。
桑若因为身体的缘故一直闭门不出,父亲便托人送了些补身子的药过去,回来的时候整个人都有些恍惚,步履踉跄。
我心一沉,疾步上前搀住他。
父亲侧首,勉力对着他唯一的小女儿微笑,轻声叫我的名字:“菀菀。”
我小心翼翼扶着他,应了一声。
他摸了摸我侧脸,叹了口气:“瘦了。”就着斑驳的日光看了看我所穿衣裙,又补充道,“天这么冷,你穿得也太少了。”
我默然低头。
在三月暖风暄暄中,父亲爱怜地注视着我:“我累了,先回房了。有事便和少卿商量商量,夫妻间,还有什么不可以解决的呢?”
他还在说,好像一切都不知道的模样絮絮叨叨在说,以夫妻相处之道劝说他这辈子最放心不下的小女儿隐忍、贤惠,和善良。
在金色阳光下,我眼睁睁看着父亲慢慢往回走。往回走,直至离开我的视线。
我的父亲死了,自尽于深夜。
我紧紧地抱着父亲,仰面悲鸣。服侍的奴婢俯身长跪,号啕着请求让老爷入土为安。我沉默注视他们将父亲自我双手缓慢剥离,那种疼痛,像是在一人心头,生生剜下血肉。
董少卿听到消息自桑若院中赶过来。我站起来,仰头冷冷注视那个背光站在门外的男子。
他犹豫叫我:“菀菀……”
我注视着他,有些好奇:“我们沈家,可从来没有欠过你什么,从来没有。”
他面上不忍,局促着走近我想要解释什么,但是我已经听不进去,我想到的是那个夜晚,委身今上那个生不如死的夜晚,父亲一夜白得头发,死的时候怎么都阖不上的双目……我抬高眼睛,从门内望着扶门而立男子,将那些怨毒的、绝望的、无告的愤怒冷却,融入其后如诅咒般的句子,血色残阳里,我静静地看着他:“我不会让你死,但是我会让任何你爱的,所有人,生不如死。”
他有些手足无措,绝望地看着我,在金色斜阳下化成一朵苦笑。
五:
我做了今上的妃子,那个只比我父亲小三岁的中年男子众多女人中的一个。
商有妲己,夏有褒姒,周有妹喜,历代诸朝,最不缺的便是亡国的君王与使之亡国的女子,只因大臣贤相都不愿承认,这偌大天下原本就是靠女人一杆细腰擎住的。
今上之于我的宠爱,业已超过那些臣子所能想象。
他夜夜宿于我殿中,以赏赐之充沛来弥补他年渐老气的岁月,和无法为济的精力。每自凝睇我时,他都会喃喃开口:“朕一直觉得愧对你,你正年轻,而朕……”
我娇笑着用手捂住他双唇,宫中一日,世间千年,时间亦足够让我学会如何将笑意融入媚骨之内,如何用娇嗔赌气取悦那年界衰老的中年男子,如何在宫廷内学会虚张声势,狐假虎威。都说相由心生,深夜揽镜自照,我都害怕,这样歹毒的心肠,怎配拥有如此纯净的面容。
宫中并无劲敌,除却岁月,这样若无其事却又凶险恶毒。
有时候前往上书房为今上送茶水的时候,在等候面见的朝臣之中还是能遇见董少卿,不过时不与昔,今日我是贵主,他是微臣,他有稍微迟疑,亦不得不随那些趋炎附势的臣子一样相继过来,朝我请安。我对着他略笑了笑,微扬下巴:“董大人可曾安好?”
他垂首,看不出情绪,只有简简单单的一个字:“好。”
十指无意识扣进肉体,将所有可能爆发的怒意遏于心口,我冷冷地打量他:“听闻董夫人有喜,我独自在这深宫颇为寂寞,等得空了烦请董夫人多到宫中陪我说说话。”
他猛然抬头直视我。
我提起裙裾缓缓靠近他,媚笑着附在他耳边低声道:“放心,我还不至于对她怎么样。”
桑若在我面前最多的举止便是深深垂头,这样弱不禁风且惹人爱怜。我淡笑着将一盅冒着热气的杯盏推到她面前,她惊惧地抬头看我,陡然变色。
我笑了笑,漫步经心道:“不要以为我不知道,当年你为保董少卿仕途太平,偷偷在我的药中加了一味春药,借董少卿之名将我送到陛下枕边……”
桑若苍白弱纸的双颊失却最后一点血色,喃喃道:“不可能,你怎么会知道?”
“有些事,想一想就能明白。”我笑了,单手抚上她被毁的侧脸,压低声音,“当日,你曾说我在给你安胎的补药里加了一味藏红花?如今,现在只有我们在,不如就将这杯茶给喝了吧。”
她竭力挣扎,却被左右服侍的宫人挟持住灌水喝。惊慌之下,她索性扬声朝殿外高呼少卿的名讳,乍听得她求救,原本依礼守在门外的董少卿推开小黄门,疾步奔入殿内,扬袖挡在桑若身前。他看着我,艰难道:“菀菀,你……”
“这里放了藏红花,我看她敢不敢喝。”我挑眉,直视他。
董少卿凝眉,在他复杂目光的注视下我徐徐饮下那据说放了毒药的茶水,朝他亮了亮杯底,淡淡道:“我只是想要告诉你,我没有害过桑若,更不会害她肚子里的孩子。”
董少卿怔了怔。
我漫不经心地笑了:“我还要让你知道,你不仅没有心,还瞎了眼睛。”
在前所未有的寂静中,他仰首闭目,似乎正在以这种方式平息内心悸动。在长久的静默中,他终于低低地开口:“菀菀,很多事情,都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拎着裙摆,略略往后退了一点,冷冷地看他微微发红的双眸:“我更愿望相信我亲眼所见。”
他那样看着我,隔着尘世的风和海,隔着不能抵达的来世来路,朝阳透过薄云染上他熏红的双眸,似乎我们第一次见到时的模样,风姿奕奕,以漫不经心的姿态徐徐行经我身畔……那毕竟是我爱过的人,我拼劲全身力气想要白头偕老的男子。
目中有我看不透的悲怆和难言,董少卿哑声开口:“那天你发烧喝的药是桑若送过来的,我一直以为你贪图富贵所以从了陛下……”我从没见过他有这样绝望的神情,“我对不起你,桑若也对不起你。如果我早一点知道,如果……菀菀,如若能重新回头……”
他目中浮起哀伤,低低发问:“菀菀,我们到底是哪里走错了?”
仓促掩盖此刻动容,我略笑了笑,朝他道:“明日子时,玄德门。”
六:
当夜今上来我殿中,我命人呈上莲子银耳羹,陪着他尽兴喝了半碗。烛光袅娜,行过半盏的工夫,他精力似有不支,我让侍女扶着他去内殿安置。
从娘家带来的侍女替我端来解药,饮过之后换上普通宫女的衣裙,确认今上暂时不会醒来之后披着夜色,独自往花园深处走去。
更深露重,簌簌行于月光晦暗,此时入夜并无行走的人,纵然有人经过也只是行色匆匆。
服侍的奴婢心中惴惴,她问我:“这样做,娘娘值得吗?”
没有值不值得,我这一生,原本就不是为了值得与否活下来的。
等过了三刻左右,天生辰光微亮,原本避于扶桑花丛下的董少卿缓步走出,视线相接于秋风瑟瑟的庭院,其间落叶阵阵,繁花无声。
他目光复杂。我想起多年前,我刚刚嫁给他,少女情怀在心爱的男子面前多么尴尬,又是多么紧张,总希望将自己最好的一面展露给对方看,而他却有个心心爱着的女子。
那时候我就是这样看着他,欣喜又伤心,难过又倔犟。
就这样漫不经心把当年爱恋他的故事闲闲讲给他听。还有那盅汤,我笑问他:“你还记得吗?那时候我天天炖汤给你喝,熬了几个时辰,就怕府中厨子不和你口味,便亲自守在炉火面前。”我淡淡瞧了他微微颤抖的身躯,和慢慢褪去颜色的两颊,轻声道,“你忘记了吧,你在沈家住了三年六个月,我整整给你煲了三年六个月的汤……”
终于无法忍受,他单手扶住扶桑花,剧烈晃动。他抬高赤红双眸,紧紧看定我,艰难道:“对不起,菀菀。”
用对不起三个字伤人真是何其简单的事情。
我伸手捋了捋头发,想到了父亲,便笑着和他继续道:“那时候父亲多喜欢你,总觉得我任性,配不上你,只是他死了,他死得这么早。他死之前,还劝我要和你好好生活,好好活下去。”我漫不经心说着最残忍的话,眼泪却落下来,一滴一滴溅到手背上。
他终于忍受不住,踉跄着错步上前,展臂,几乎是恶狠狠地拥住我,温润的唇瓣擦过我冰冷的额头,哑声艰难道:“对不起……”
那些湮灭在遥远年代里不可触摸的往事,那些相见不能承认的伤害,他低首用额头与我的相触,怆然拥抱,仿若拥紧错失的多年时光。
那是我从少女时代开始等待起来的拥抱,而他到来的时候,我已经不适合拥有他,而董少卿,也一样。
他不知道,沈菀早就疯了,疯在三月之前那个夜晚,被她侍妾灌下春药送到今上房中的那个生不如死的晚上,也醒在三月后的那个夜晚,她丈夫说对不起的夜晚。
七:
我略笑了笑,漫步经心取下头上发簪狠狠刺入他的肩膀。他吃痛后退数步,捂住伤口,有些茫然。
星辉洒遍泛着冷波的湖面,冷光遍野。而我所想要的一切,都在我预料以内。按计划等候在御花园入口处的侍女匆匆上前扶着我,略显惊慌往后看,正撞见原本应当在殿内深睡的今上疾步而来,携着九月初秋冰冷的风和炽热的目光。
没有分毫差错,我瑟缩着往后退,惊慌之中原本握在手上的银簪哐当跌落地面。今上解下披风裹住我,俯身将我从泥泞小道抱起,不辨喜怒的神色扫过我,掉落地面染血的银簪,俯跪于地的一干仆从,以及以同样的姿态跪在他面前的,董少卿。
我想,真是没有比亲眼所见,更强有力的污蔑。
今上伸手替我拂去挣扎中凌乱的发丝,我瑟缩在他怀内,那些经年的委屈、伤害、绝望和放弃如此强大,强大到不需要多少伪装,已经哽咽到难以为继:“董大人邀我深夜来此,说有沈家的消息要相告于我,只是……沈菀怎么都没想到……”
今上沉了沉眸色,冷冷看向垂首跪于地面的董少卿:“菀菀说的,是真的吗?”
我啜泣着,伸手将事先准备好的,预备在对方辩白时作为证供的禁令举高,呈到他面前,:“这是董大人交给菀菀的,说是可以助我逃出宫中……”我难遏哭声,索性便埋首于他怀中,“董大人竟做小人之事,沈菀怎么都想不到,他竟逼迫沈菀……”
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董少卿的神情。
他极度震惊,陡然转换的场景和现实让他有片刻的愣怔,而我所预料的诡辩、争执、污蔑,乃至为自己辩解的理由,他一个字都没有出口。
在几乎凝结的时光中,他仰首,静静看了一眼伏在今上怀内的我。此前动容哭泣的双眸微微一颤,旋即化成一朵淡若云烟的苦涩笑意。
他,只是笑了笑,在前所未有的震惊中朝今上深深俯首谢罪:“对,是微臣深夜邀娘娘于此,一切,全都是微臣的错。”
在被今上抱离之前,我攀着他肩头回望那个跪在一群小黄门中间,神色淡淡的男子,将自己蜷成小小的一团,捂住眼睛,终于极小声极小声地哭了出来。
我也不知道,我们到底是哪里走错了。
八:
翌日,以“举止不端,奉主无状”为由,董少卿被削去功名利禄,贬为庶民终生不再录用。
他离开长安前一日我去狱中瞧他,他默然独坐一隅,在离开之前被他唤住。他背对着我,低低道:“菀菀,我不怨你。”
痛得连身体都在发抖,我扶着牢狱粗木一点点往下滑,直到与他平视的高度。我盯着他,紧紧盯着他:“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说这种话,你不配,你永远不配。”
董少卿看了我一会儿,重又低下头,淡淡苦笑:“你尽管恨我吧,是我负了你。”
我怔住,所有怨怼、怨毒、怨恨的话语都得不到宣泄的余地,它们奔腾在我眼底,幻化成冰冷的泪珠。我站起来,慢慢往来时的方向走去,而每一步的行走却仿若在刀尖之上,痛楚毫无阻碍直达心底,雾色浮起盛满眼眶,让我难再辨清方向。
我仰面,承接来自烈日漫不经心的直射。于心底告诉自己,从此,没有沈菀。
有的,也只是困顿孤城的,我自己。
转载请注明:http://www.dongyamedia.com/yzzl/1074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