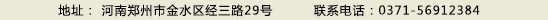戏子爱情胭脂雪,红颜泪
我是个唱曲儿的,别的就不多说了,不要纠结我到底是哪个明星,我不会说,说了你们也不一定认识我,而且这个故事的主角儿也不是我。
我能有今天这样的成就,真的是多亏了我们家祖祖辈辈嗓子亮堂,尤其是我外婆。
听我母亲说,当年的上海大戏院,只要是我外婆登台,黑白商政各界有头有脸的人物一准儿会来捧场,而更让我感兴趣的是,外婆还有另一个身份。
她是那个时候的上海花国里,最特殊的舞女。
只可惜外婆走得早,她的故事我从来没有机会能听到她亲口讲述,她曾艳惊四座的唱腔也仅仅留存在一张没有封套的老旧唱片里。
今年初春,父亲久病离世,等一切打点好已经是深秋,我和母亲一起搬回了北城老宅。
今天一早起来,我们本打算继续整理行李,谁知刚开始动手我就发现了一本记事本,硬面精装,透着一股怀念的气息,虽然封皮已经被手掌摩挲得变了颜色,但却是很仔细的收置在一只铁盒子里。
我随手一翻,纸页间夹着什么东西,很容易翻开。
取出来看,那是一张剪了花边的黑白照片,照片中的女子端正的对着镜头,她生着标准的瓜子脸,薄唇微抿,尽管没有笑容,那神色也让人觉得娴雅温润。
看那眉眼可不正是母亲年轻的模样吗。
我合上记事本,连同照片一起递给母亲,顺口调侃道:“保存的这么好不会是日记吧,您还真有格调,快找个地方藏好不然我偷看了啊。”
“日记?”母亲一脸疑惑的接过去,“我哪有写过什么日记。”
待她看过记事本的扉页,便会心般笑了。
“你不是一直想听你外婆讲她的故事么,”母亲又把记事本递回给我,“这日记是你外婆的。”
扉页右下角的字迹颀长灵秀。
齐门苏旖年。
我有些不解:“外婆不是姓丁吗?”
母亲笑:“其中因由不就都在你手上。”
我心下纳闷,整理行李的事看来要稍作推迟了。
沏了壶茶,坐在老宅宽敞的阳台上,我认认真真的翻开了这本记事本。
因为年代久远,有些字迹已经模糊,有些语句晦涩难懂,我一边看,一边把日记的内容整理记录下来。
然而这并非仅仅只是一本日记。
这是一个完整的故事,那故事中的女子,唱尽了人生苦楚,见证了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穿梭于两个世界之间的一场风云变幻。
民国十八年,正月十四,北城,阴,有雪。
我第一次被生命置身于一场死亡。
我的母亲杀死了我的孩子。
从去年春天开始的大旱,持久而绵长,北城的人们在不知不觉之中,已经被卷入一场多年以后仍然让人谈之变色的浩劫。
夏秋无雨,冬春无雪,年馑把北城的人变成了田里的麦子,把北城的风变成了镰刀的利刃,风轻轻一吹,人们便像黄了的麦子遇上锋利的镰刀,一茬接着一茬倒下去。
我躺在床上,昏昏沉沉的发着低烧。
窗外天空阴沉,窗花好像没有涂够浆糊,有气无力的挂在玻璃上。
母亲端着药走进来,轻声问道:“醒着么?起来把药喝了吧。”
我点点头,费力的撑起身子接过碗来,青花瓷碗泛着一层旧旧的黄,一道黑色的裂痕从碗口绽到碗底。
母亲看着我一口口喝下药,轻轻叹了口气,收走了碗,就坐在床头的竹椅上。
我重新躺下,迷迷糊糊的睡过去。
不知又过了多久,似乎感到母亲替我掖了掖被角,在我耳边低语一句。
“对不起。”
我蓦然惊醒,汗水浸湿了脑后的枕头,胃里翻江倒海,全身覆了一层电流般阵阵发麻。
我挣扎着爬到床边,张嘴便吐,一直吐得眼前忽明忽暗,脑中嗡嗡作响。
母亲的声音像是泡在水缸里,她说:“没事的,就好了。”
我抬起头,她端着一只瓷盆守在我面前,静静的看着我,脸色苍白得让我害怕。
为什么要这样看着我?我到底怎么了?
我猛地推开她,惊恐的尖叫:“你让我喝了什么!”
她摔在地上,抿着嘴不说话。
腹中一阵绞痛传来,我一把抓在自己的小腹上,忽然间明白了。
母亲想杀的不是我。
我摇摇晃晃的倒回床上。
她想杀死的,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啊!
腹中凭空生出了一只手,捣刮着捏碎着掏空着,那尖长的指尖几乎就要由腹内刺穿我的皮肉,我想要翻滚,却只有手指微微抽动,我想要哭喊,却只有嘴唇微微颤抖。
一股接一股温热的液体争相由体内涌出,濡湿了身下的床铺,转瞬冰凉。
几粒莹白的碎末落在窗棂上,化成星星点点的水迹。
如果什么都可以像雪一样,总有一天会在太阳底下消失得不留一点痕迹,是不是件好事呢?
远近的欢呼声顿时陆陆续续飘向空中。
“下雪啦!”“庄稼有救啦!”“不用饿肚子啦!”
而那场梦一般的细雪,并没能从持续三年的大饥荒中拯救北城。
于是很多年以来,我一直都认为,那场雪,只不过是为了融化我那不知何去何从的悲伤。
那一年我十六岁,我肚子里孩子的父亲,是我母亲的妹夫。
我在北城一个没有什么名气的坤班里长大,母亲在班子里不温不火的唱着青衣,唱花旦的则是母亲的妹妹。
每天阳光最好的时候,我都搬着小板凳坐在戏班的院子门口,等着母亲和姨娘上台练唱。
一开始街坊邻里也还图个新鲜,里三层外三层围着院子看,甚至在院墙外搭了梯子,也要探个头进来。
时间一长便冷清下来,照旧每天来看的除了我,就只剩几个正经爱家。
齐老太便是其中一位。
齐老太姓齐,独自住在离戏班不远的小院,她的院子里种着一棵大树,这就是我所知所有关于她的事情。
她总是满眼渴望的看着戏台说:“现在真好哇,原来我们那个时候,坤角儿是根本不让上台的,任你再想唱,只要是个闺女,就不成。”
我见她如此动容,便在身边的位置为她多备了把竹椅。
她十分欢喜,摸着我的头顶问:“闺女叫什么名儿?”
我说我叫丁陌,她就又问:“陌闺女喜欢唱曲儿不?”
我使劲儿点头,齐老太也笑着点头。
又过去一段时间,齐老太突然不再来了。
我看着身边空了好几天的竹椅,终于趁母亲不注意溜出了院子。
扒在齐老太家的小院门口,我小心翼翼的伸出头朝里看,齐老太就坐在那棵大树下的藤椅里,阳光穿过树叶的缝隙垂下,藤椅在那光束中摇啊摇。
齐老太看见了我,便冲我招手:“陌闺女,你来!”
我跑进院子,跟她一起钻在大树下,她说:“阿婆我老了,想听曲儿也走不动了,陌闺女给我唱一段儿吧。”
我点头,仰起脸就唱,微风吹过,头顶枝叶摩挲,发出沙沙的声响。
齐老太笑得合不拢嘴,直说:“好,亮堂!真亮堂!”
我也揪着衣角笑。
齐老太把我拉到身边,摸摸我的腹背:“闺女有副好嗓子啊,若是行气上再做修整,可是不得了。”
看我一脸不解的模样,她又拍拍我的头顶说:“想不想唱得更好?”
我连忙点头。
“那你按我所说呼吸吐纳的法门,再唱一次。”齐老太轻轻一点我的鼻子。
我再开口,高亢嘹亮相较此前不可同日而语。
齐老太的身体时好时坏,好时她便来戏班里听曲儿,坏时我便到那大树下唱与她听,除了唱腔,她也教我一些身段儿,就这样很快我便长到了十五岁。
北城大旱,哀鸿遍野,民不聊生,“饥饿”成了人们心中比“兵匪”更加猛烈的恐惧。
戏班的存粮勒紧腰带也只够大家勉强吃到年底,挑班的老旦终日愁容满面:“如今粮比银贵,哪里还有人顾得上花心思听曲看戏。”
“听说邻县的徐老爷好这个,”台上的坤生接话道,“他近日要办大寿,到时定会请戏班子前去贺场。”
老旦叹口气摇摇头:“徐家是大户人家,十里八乡的戏班子都抢着接活儿,我们一个没有名头的坤班,如何赢得过,且不说…”
她看了一眼我姨娘。
姨娘去年嫁了人,怀里抱着刚满周岁的孩子。
我见人人都锁紧了眉,便拉了拉母亲的衣襟,悄声说:“娘,我能唱。”
母亲抿起嘴,没有在意我的话,倒是老旦听了苦笑一声:“陌丫头也长大了,若是想唱,等过了这回年馑,以后便带着你。”
坤生坐在戏台上,拍拍地板朝我喊:“陌丫头,能唱就上来亮亮嗓子,给大伙儿醒醒神。”
我望着母亲,她轻轻在我背上一推,我便顺势走上台去。
戏台铺着红布,背板也钉着红布,台上台下零星散坐着那些个看着我长大的人,远处的蓝天干净得像水洗过。
待一曲终了,周围安静得有如停止了时间。
连母亲也瞪圆了双眼看着我,微张了嘴却说不出话。
我揪紧了衣角等着他们做出反应,不知是因为兴奋还是紧张,脸颊有些发烫。
老旦回过神来,舒了口气叹道:“陌丫头,你这是什么时候练的唱?”
不等我回话,坤生已经一捶掌心大笑:“甭管什么时候练的,那徐老爷的寿辰咱们是去定了!”
老旦便也笑着问我:“想唱哪出?”
我看了看母亲,答:“玉堂春。”
“还是你最喜爱的戏本。”老旦也对母亲道,“那么把戏袍改一改,就唱玉堂春!”
母亲柔柔的点头。
坤生跳起来,一把将我揽进怀里,用力揉着我的头发。
我们在一片鲜红里笑作一团。
然而最后,我却始终没能站上那方戏台。
那天趁戏班外出,我偷偷穿上母亲改好的戏袍,爬上戏台向着空旷的院子轻声念着唱词。
忽然之间,眼前的天空打了个旋儿,地板腾空而起击中了我的后脑。
一阵酒气灌进嘴里,我这才意识到是自己摔倒在了地板上,正死死压在我身上的,是我母亲的妹夫,那个被我唤作“姨丈”的男人。
他像头牲畜胡乱拱动着,他嘴里的湿气在我的脖颈处凝成一片湿冷,他贴在我耳边含糊不清地笑:“丫头,乖啊,乖…”
我一惊,尖着嗓子哭叫起来。
他一手抓着我的头发,一手撕扯着我身上的戏袍,笑得更加疯狂:“丫头你知道不,你曲儿唱得可勾人,一出声儿我就想扒光了你让你喊,就这么给我喊啊…”
一股血气从胃里翻涌上来,堵在了嗓子眼儿。
我霎时哑了。
我咬着嘴唇挥着拳头,推搡捶打。
可我的手臂太瘦了,如果不是荒年,我一定要让母亲每天多给我盛一碗米饭,我想要长些力气。
鲜艳的台布染红了院子染红了天,染红了我的双眼,我直愣愣的盯着院门口,等着母亲回来。
刚满周岁的小表弟颠颠儿的从里屋跑出来,绕着院子跑到台边,扒着台子探着头,朝我露出一脸无比怪异的表情。
原来如此幼小的孩子,竟已懂得做出这样的表情。
母亲直到入了夜才回来。
我抱着撕破的戏袍走到母亲身边,母亲接过去看看,轻轻叹了口气:“娘不让你穿,不就是怕你不小心耽误了事,等过几天到徐老爷府上唱完,你想怎么穿不行。”
说着她便伸手去摸针线筐,取出一卷红线。
那丝丝缕缕刺眼的鲜红啊。
我眼眶一热,一头扑进她怀里,再也抑制不住的放声大哭。
母亲脸上的表情从疑惑不解到惊惶失色再到不知所措,最后她沉默半晌轻声对我说:“算了吧,反正都过去了,别再说了。”
的确许多伤口就算放置不管也能自然愈合,但也有一些伤口,无论再怎样修补却终是要了人的性命。
我并不认为这是用“过去了”便可以敷衍的过去。
是不是我讲得不够清楚,是不是你还不明白。
我抢过母亲手里的戏袍扔在地上,扯着她的胳膊继续哭诉。
“行了!”母亲猛地站起来,一个巴掌重重的扇在了我脸上,“不要哭了!”
是不是因为我哭得太厉害,所以你才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我呆呆的摸了摸发烫的脸颊。
好的,那么我不再哭了,这样你可以听我说了吗,娘啊。
请你听我说啊。
徐老爷寿辰当日,我躲在齐老太的院子里,缩在那棵大树下,拿着捡来的树枝一下下的挖着土。
齐老太说:“闺女,给阿婆唱段曲儿吧。”
我摇头,她便靠进藤椅里,安静的闭着眼。
风一吹,大树抖落漫天的枯叶。
齐老太悠悠道:“北城真冷啊…”
我仰起头,数着日渐光秃的枝桠。
若说是在那时,我的心中初次隐隐萌出了对南国温暖的向往,后来母亲在元宵前一天端给我的那碗药,便是彻底断送了我对北城所有的念想。
她杀死了我的孩子,杀死了我那过去唯一的证据。
↓↓↓点击阅读原文
赞赏
转载请注明:http://www.dongyamedia.com/zzyz/956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