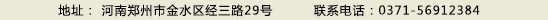一个竟被六个皇帝疯抢了60年的女人,她究
:恩怨恨绝
刻箭指向辰时,顷刻间八音迭起,玉振金声,从鸿图华构的太和殿响起,越过黑压压行着三跪九叩大礼的群臣的头顶,穿过流丹飞阁,从雕栏玉砌到尺椽片瓦,光辉与灰暗之有一墙之隔。
金碧辉煌的皇宫内也有杂草丛生,冷僻荒凉之地,那是皇恩不及,春风不到的地方,里面的生命唯有枯萎的命运。
寒风呼啸,院中桃花细逐杨花落,让人遗忘此时正值春意盎然的四月。
屋内斜依在美人榻上长孙纬彤,慵懒地拨弄着薰笼中燃尽的香尘,铜漏壶中的流水缓缓滴露铜盆中,溅出清脆的响声,一响、一响,嘀嗒嘀嗒,甚是有趣,怎么以前从没未聆听过,浅笑着意识到,从前住的昭阳殿,整日里珠围翠绕,这般微弱的声响,早就轻而易举得淹没在人声中了,哪里还能被人所留意。
“长孙氏接旨—”
院外传来提着脖子的鸭子般尖细的嗓音,长孙纬彤柳眉微蹙,轻嗤一声,没有搭理,继续挑弄着薰笼内零散火星。
“罪妇长孙氏还不快出来接旨——”
话音落下许久,仍是不见屋内的人出来接旨,掌事太监李富清狠瞪了眼身后忍不住发出笑声的小太监,不悦地甩着拂尘,推开木门,走进屋中,撇了眼小太监,小太监明意,紧低着头端着木盘走到榻前,低声唤道:“娘娘——”
长孙纬彤轻飘了眼所呈之物,一把锋利匕首,一瓶毒药,叠了三折的白绫,双指揉捻着干花,冷笑道:“今儿十三,宜入殓,忌嫁娶,皇帝还是疼我。”
李富清责怪着小太监:“长孙氏失序无德,华而不实,朋煽朝廷,早已被废,而今此处,哪来的娘娘。”
长孙纬彤卸下翡翠耳坠,放在绣帕上,对小太监说:“还给你们的主子。”
小太监犹豫不决,迟迟不敢上前,宫中无人不晓这对耳坠是吐蕃进贡贡品,绝世无双,圣上亲手为纬彤戴上,以示对她独一无二的珍爱,小太监小心劝着:“娘娘不必这样绝情,圣上……圣上还是念旧情的。”
“哼,念旧情?”长孙纬彤的心猛然一抽,翡翠清冽的绿光似毒针深深刺入心扉,自己背负祸国殃民的妖妃之名,替他铲除异己,乾坤天青后,随意听了几句蜚语,恩情便断了,什么情深,什么胜宠,什么箴言,自己怎么就对君王之情认了真呢,真是可笑。
长孙纬彤从塌下走下,小太监忙退步,只见她冷眼对着李富清说:“金銮殿上受凤印的那位也是长孙氏,你的失序无德,指的是她吗?”
“罪妇,你还不知悔改!竟敢对当今皇后大不敬!”
她眼神如碎玉,凌冽含恨,环视殿中,处处尽显雕饰,同宫中叠加无数面具的人别无两样,连亲妹妹都可以不念血浓深情对自己下毒手。
纬彤目视无人的走出殿外,一缕微弱的阳光洒落在她消瘦的肩上,许久没晒过太阳了,剥落下木栏上裂开的朱漆,心中一遍遍念着那两个名字,萧炫,长孙柔嘉,萧炫,长孙柔嘉。
远处清脆的鞭炮声,她听得清清楚楚,可怎么都感受不到痛了,她轻抚着小腹,几天前,那里还住着一个生命,那天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刻在骨子里,拔不出来,抹不去,化成毒液,流经所有脉络,焚烧一切。
当李福清宣读完废妃诏书,殿内所有人屏住呼吸侧立在旁,大家都不敢想象这位心高气傲,宠声震天响的贵妃娘娘的反应,而她却是出奇的冷静与木然。
纬彤接过绢帛,忽然想起在王府中,太子妃邦媛被废,那如撕碎的画扇般狰狞着诅咒自己不得善终的脸,长叹一口气,殿内的寂静反倒让人更加不安,齐齐跪在地上,求着纬彤不要难为奴婢们了。
纬彤见此,不解笑道:“如今我已是打入冷宫的废妃了,你们求我作何,快去仁明殿里拜另外那位长孙氏吧。”说话间,肚里的小家伙又踢了下她,纬彤皱起了眉,对李福清说:“我要面圣。”
批阅奏折的萧炫听闻纬彤在殿外求见,不假思索道:“不见。”
过了三个时辰,听见窗外小太监们的窃窃私语,浮躁不已喊道:“私下说着什么呢?”
小太监忙慌张进来,犹豫再三,怯怯诺诺的回应道:“娘娘……长孙氏仍跪在殿外。”
天空响起了闷雷,空气湿潮,如密织在一起的网。萧炫心口闷得很,丢下手中的笔,命人将窗户推开,雷鸣电闪,顷刻间骤雨袭来,雨随风飘落在宣纸上,那纸封后诏书上“长孙柔嘉”四个字的墨晕染开来,萧炫重新平铺开一张宣纸,行云流水,无不是褒扬之词,搜罗天下美名全贯于一个人之上,写到“长孙”二字,笔锋忽迟疑,一块墨迹迅速晕开,他想再提笔,“柔”字怎样都下不了笔,又将纸揉成一团,狠狠砸到地上。
“宣。”
萧炫听见门扉推开声,转身刹那,不免一惊,记忆里的女子从来都是光艳动天下的,而今衣衫淋透,面色苍凉,眼睛波澜不惊,一屡薄冰,扑通一声,直直跪在地上,神情坚定,畏惧的直视着自己。
“你还有脸见孤。”
她倔强的抬起头,望着高高在上的萧炫说:“莫须有的罪名,我不认。”
萧炫勃然大怒,指着纬彤怒斥道:“你还要孤把那奸夫拉出来,看着你们上演生离死别桥段吗!”
纬彤的心抽悸了一下,如被蛇蝎蛰了般疼,眼眶通红,强忍着泪,哽噎许久:“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我十五岁入府,将一生小心翼翼托付给你,三皇子与你争夺太子之位,围猎场上的暗箭是我为你挡的,苏家造反,苏清漪的毒酒是我替你喝下,现在你登帝位,以我为刃,除去荆棘,我被万人唾骂,祸国殃民,背负妖姬之名。而你宁愿信那些不相干的人,都不愿意信你的枕边人!”
萧炫拔出腰间佩剑,抵在她的脖子上:“孤何时又负过你?专房擅宠,让你主断内事,不执妃礼,六宫莫与为比,无人不知这是你我的天下!”
“好一个不相干!你是说你的亲妹妹在污蔑你吗?柔嘉怎么可能会无故害你,如不是她对孤一片真情,说出你淫乱后宫的实情,我到底要被你骗多久!你对得起孤吗?”萧炫恨意油然而生,紧盯着纬彤微隆起的小腹,纬彤面容失色,下意识护住了小腹,不敢猜测他的意图,凉意席卷而来,“这是你亲骨肉!”
“事到如今,我还能信你吗?”萧炫话毕。
纬彤忽然放声大笑起来,笑声惊起枝头杜鹃,凄怨的啼叫与惨烈的笑声交织在一起,“哈哈哈,我原先还不信我对你的真情就抵不过那贱人的三言两语!呵,现在我信了,你能容忍一个对至亲都下得去手的人,不过是因为你和她一样冷血无情!”
话音未落,纬彤的脸上立刻留下一个火红的掌印,雨水顺着乌黑云发从额滑过面颊,更加疼痛,纬彤咬着牙,强笑着:“看来您是承认了。”
萧炫头皮发麻,横眉竖起,抄起案上的砚台砸向纬彤,“你不仅不知悔改,还违逆杵上!长孙纬彤,孤是真的把你宠坏了!”她不服软,那么他就亲自一根根的掰断她的骨头,让她粉身碎骨。
墨点洒落房间四处,墨汁渗入额头伤口里,血腥混着墨香,手指一抹,纬彤见手指上的腥红色,轻蔑一笑:“你和三岁孩童发脾气有什么两样。”
“孤倒要看看你能嘴硬到什么时候!”萧炫彻底勃然大怒,一脚踹到她的小腹上,剧痛席卷全身,纬彤紧紧护着腹部,欲想奋力爬起来,可手始终无力,几番跌倒在地上,一个阴影覆在白皙如玉的手背上,很快,十指连心的疼叠加而来,屋内很快响起骨头碎裂的声音,纬彤紧咬着舌头,不肯吭一声,口中浓烈的血腥让她忍不住想作呕,汗水与雨水不分了彼此。
“萧炫!”
这是惊泣天地绝望的呐喊,萧炫移开的脚,脚下血肉模糊,他俯身捏着纬彤的下巴,用手指拂去她咬破的唇旁的血迹,斥满血丝的墨眸死侍一般瞪着自己。
“这双眼睛,孤不喜欢,挖掉吧。”他将纬彤的脸甩到一旁,语气云淡风轻,小太监却吓得面无血色,跪到地上。
匍匐在地上的纬彤挣扎着,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抓住萧炫的衣角,这身黄袍留下永远都洗不掉的血印,她已无任何言语,诅咒也好,恨意也罢,喉咙滚烫,只发出困兽样呜呜的低吟。
萧炫回身一脚踹到她的小腹上,将她踢到墙角,他是九五至尊,万人臣服,天下都是自己的,她再如何惊艳天下,终究也是脚下的蝼蚁,她的权,她的骄傲,都是自己给的,那也可以亲手毁的一干二净。
纬彤卷曲着身子,浑身冰凉,身下一摊血,眼前恍惚一片,瞳孔放开,难以置信地摸着自像是颗秋天里饱满的麦子的腹部,两行清泪自然滑落,“孩子--”,这是她的孩子,如小刀挑破肌肤,用最坚韧的刀尖鉆着自己的心,一寸一寸的插进去,不留丝毫喘息,嘴角快裂到了耳根,彻骨的恐惧,体下血流不止,她颤抖着身子,拼命朝向爬着,身后拖出长长的血迹,不顾一切的抓住萧炫的脚踝,无助的低声撕鸣着:“救救他,救救他,求你救救他。”
萧炫头也没回,摔门而去,他带走了纬彤最后一丝光,长廊内彻响着呕心抽肠的哭声。
愈来愈响的鞭炮声将纬彤从噩梦般的过去中拉回,杜鹃啼鸣似一声声的“不如归去,不如归去,不如归去。”
体内住进去一个工匠,拿着锥子反反复复鑿刻着那两个名字,“萧炫,萧炫,长孙柔嘉,长孙柔嘉。”,踩过的桃花被她狠狠碾到土里,此时已是无恨无悲的了,那日从殿内被人抬出来,自己早就烧成了灰烬,血也凉了,热不起来,她回头看了眼要夺她性命的三样物件,“我万万不要死在这群薄情之人的手里,你们杀我孩儿,致我于深渊,我死后势必化成厉鬼夜夜绕你们不得安宁。”在金鼓锣鸣中,傲睨自若地纵身跃入深井中。
:引狼入室
指尖被丝绒样的线缠绕,耳畔依稀传来三两人的谈论声,长孙纬彤缓缓睁开眼,见绕在三根手指上穿过屏风的细细丝线,心里一时欢喜,脱口而出:“我的孩子保住了吗?”
屏风后传来一阵嬉笑声,挽着双环髻,身着豆绿月华裙的小姑娘走到她面前,笑盈盈地说:“姐姐怕是从马上摔糊涂了,你还待嫁闺中,怎么就有了孩子呢。”
看这姑娘的脸,心头一震,柔嘉!定了神,仔细打量一番,是柔嘉!但是许多年前,正值豆蔻的柔嘉。
柔嘉看着紧盯着自己看的纬彤,捂着嘴,笑起来,“姐姐?哈,你不会连你亲妹妹都不记得了吧。”
纬彤的手轻抚在小腹上,杏眼微眯,冷笑一声道:“你,几世轮回,我都忘不掉的。”
“那就好,姐姐,你一定记得今日是父亲大人半百寿辰吧。我要去准备今夜寿宴上的独舞,就不陪姐姐了,你在屋内好些休息。”柔嘉掩好纬彤的被角,嘱咐了大夫几句,便浅笑离开了。
纬彤冷漠地望着面面俱到的柔嘉,显露出鄙弃之情,心中唾弃着:“假慈悲。”
回想柔嘉的话,不免生起疑惑,“半百寿辰?”她命婢女拿来镜子,那是一张不见泪痕,不染纤尘的容颜,颤抖地抚上镜中澄澈的双目,忽见目中波光潋滟。这才是她,久违的自己。
纬彤放下铜镜,过往如走马灯样重回眼前,分明是柔嘉有意惊扰马儿,才使自己从马背上摔下来,无非是想独绽光彩,今夜就切任她去吧,往后的日子就另当别论了。
夜幕降临,屋外歌舞升平,纬彤厌倦地放下珠帘,轻解罗裙衣带,水雾萦绕,胜雪肌肤透着粉光,脚尖点水,初试水温,莹莹水珠挂在鬓云上,纬彤缓缓沉入水中,水淹没她的颈,她的唇,她的眉眼,如前世的最后光景一样,整个人浸入水中,窒息,沉溺,无望,她要让自己记住这种痛苦,日后加倍还给那两个人。
忽然听见窗边传来细碎声响,警惕地准备回身时,冰凉的匕首抵在颈上,她不敢轻举妄动,心想柔嘉下手也未免太早,鼻尖轻嗅,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血腥,猜想到这人大概已经负伤。
她透过水中倒影,看见一戴着面具的黑衣男子,刚想问他是不是长孙柔嘉派来的,叩门声响起,黑衣人的手猛然用力捏住玉颈,呼吸愈加困难,刀刃向上微翻,紧贴在肌肤,粗重的呼吸声,显然那个人很痛苦,一股股热潮弄得她耳后微痒,纬彤悄声说道:“你弄疼我了。”
她感觉到匕首稍轻了下,但随后又逼近她,嗓音沙哑,低沉着说:“别耍花招。”
又是一阵敲门声,门外脚步声愈来愈杂,火光冥冥,纬彤的手搭在黑衣人的手上,“我快喘不过来气了,不放不开我,我怎么赶他们走。”
“大小姐?您在屋内吗?”
黑衣人放下匕首,抵在纬彤裸露出水面的脊背上,纬彤处乱不惊的高声问屋外小厮:“屋外怎么那么吵,出什么事了吗?”
门外传来恭敬的声音:“今儿摆宴席,自然热闹些,夫人听二小姐说您醒了,打发我们来问下。”
小厮对自己说了谎,引起这么大的风波,看来这个刺客有点来头,但如果真是针对自己,也无须弄出这么大阵势来,“哦,我明儿就去给夫人请安,你们退下吧。”
“大小姐……”
听他犹豫的声音,纬彤扬声反问:“怎么?”
“夫人让我给您送药,大小姐,方便让我进来吗?”
话音刚落,黑衣人肩膀微抽搐了一下,看来是胳膊受了伤,纬彤欲想挪动身体,却被紧紧按住,匕首又贴近一丝,她只好轻笑道:“替我谢夫人关心,我已经好了,药拿给桃儿收着吧。”
“小姐真的无恙吗?还是让我……”
身后的匕首力度愈来愈轻,她看不见面具下的表情,但一定猜出伤口让他愈来愈虚弱,消耗着他的体力,这时身后传来门推开的声响,纬彤的背瞬间挺直,刚想呵斥他退下,千钧一发之际,一清脆的耳光声响起,“滚出去!你是想被挖了眼,还是斩了腿!大小姐的闺房是你们这等人能随便进的吗?”
屋外的人暂且被突然出现的柔嘉稳住了,她听见小厮说道:“二小姐来了,那就劳烦您照看大小姐了。大小姐,今日多有得罪,您大人有大量……”
纬彤打断了小厮的话:“够了,我累了。”
層层珠帘伶仃作响,让纬彤的弦又绷紧了,这个人的身份还是个迷,一定不可以被柔嘉发现,万一是个陷进怎么办。
纬彤急忙转身,也不遮拦,黑衣人猝不及防松开了手,连忙将头转侧一旁,不敢看肤如凝脂,微露酥胸的纬彤。
“你把眼睛闭上!”纬彤轻声命令道,一把拽过黑衣人,在柔嘉要绕过屏风时,将他脱入水中,扯过白丝,覆在木桶边缘,刚刚好遮住了他。
纬彤自然的提过花篮,轻撒着花瓣,水面缤纷,“今夜舞跳的如何?”
“我就是要来跟你抱怨这事的!哼,好端端的全被一个突然冒出来的刺客搅乱了,太子殿下大为不悦的提前撤了席,宴会取消了,舞也没跳。”柔嘉走到她身边,拿起朵玫瑰,嘟着小嘴,撕扯着花瓣,忽瞥见地上的血迹,心生狐疑,轻揉着纬彤的肩膀:“姐姐脚踝的伤刚好,可千万要小心些,别再添新伤。”
纬彤心思一转,莫非是她发现了吗?在水中摸索着,从黑衣人手中夺过匕首,朝着自己的胳膊划去,水浸入伤口,一阵刺痛,举起手臂,自顾自地摸着伤口,轻嗔着对柔嘉说:“妹妹的是,瞧,我刚又不小心被划破了。”
柔嘉打量了眼伤口,又瞥了眼地上的血迹,不免有些失望,转而关切地说:“看来还挺深,明儿,继续请苏大夫为你包扎下吧,那姐姐早些休息,妹妹不打扰了。”
门刚被关起,纬彤大松了口气,见水里的那人还不出来,用脚踢了下他,“出来了!”
还是没有反应,纬彤拉过挂在木架上软烟交领长衣,披在身上,拽住黑衣人的领子,提了起来,大吃一惊,那个人已在水中晕了过去,沾湿的墨漆长发零散浮在水面,连忙把他用力拖出水面,靠在木桶边缘,情急下,纬彤揭开他的面具,薄雾间面无血色,唇惨白似梨花,“萧维桢!”记忆里,这个人与世无争,一心领兵打战,后战死疆场,怎么会无端以刺客身份出现在长孙府上。
扯开他的衣襟,血液乌黑,伤口已有些化脓,“伤他的利器有毒!”纬彤有些焦急,自己如今把他留了下来,死在自己房里,更加说不清,取了一瓢凉水泼向萧维桢的脸,终于见他嘴角抽动,有了反应,捧着他的脸,对他嘱咐着:“萧维桢!你给我听着,你是以后要成为定国将军的人,这点小伤是奈何不了你的,别让我看不起你!”
萧维桢眼睛轻睁开,纬彤急忙护住胸前,“你看什么看!你点头答应我就好了!”
意识逐渐削弱的萧维桢勉强撑死点了点头,纬彤叹了口气,唇敷在伤口上,吮吸着毒血,萧维桢吃力地用手推开她,眉头紧皱,纬彤全然不顾地又扑了上去,双唇包裹着,一点点吸着毒血,终于血液澄清了许多,流出鲜红色。
纬彤擦着额头上的虚汗,取出药膏,涂抹到伤口上,“啊——”萧维桢不禁呻吟出声。
“哼,这点小痛就受不了,还带兵打战?”纬彤想起那日萧炫给予自己的苦楚,恨意涌上心头,不留神地将药膏撒多了,又传来一声痛楚,第一次见这个铁骨铮铮的汉子这样,纬彤不禁偷笑起来,取来纱布包扎好伤口,萧维桢已熟睡,纬彤拿起匕首,拍了拍他的脸,“你不仅用刀挟持我,还一览了本小姐的春光,如今蹭我的药,占我的床。萧维桢,上辈子,我们无仇无怨,这辈子,你干嘛来惹我,这次先拿你开刀!”
纬彤把面具重新带回他脸上,抱起一床新的被褥刚想走,忽听见他轻声呓语道:“好冷。”,想放下床帘的手,犹豫了,无奈摇着头,把自己的被褥又盖在他身上,仔细掩好四周的被角。
天已蒙蒙亮,忙了一晚上,虚惊一场,纬彤已无了睡意,点起一盏烛灯,坐在窗前,随意翻看起棋谱。
不知过了多久,床上微发出声响,纬彤走近,面具下传来闷闷的声音,凑近一听,“水—”
“我重生为大小姐”
纬彤急忙倒了一杯茶水,轻揭开面具,指尖轻蘸,湿润着他干枯的唇,扶过柔软的唇,如回春之手,梨花染了春风,添了胭脂。
手停留在唇峰上,另一手执着面具,试试不放下,借着橙橙微光端详起来,两弯眉不似萧炫那样风流意韵,却是格外英气抖擞,就是不知那紧闭的眼下藏着怎样的光。
萧维桢轻咳一声,纬彤回过神,把面具盖上,蹑手蹑脚的回到桌前,眼睛有些酸涩,伸了一个懒腰,轻伏在案上小鎴。
院中黄鹂鸣翠柳,暖暖春意透过薄窗笼罩在纬彤身上,她微微睁开眼睛,余光瞟见萧维桢坐在床边,连忙紧闭起眼,继续装睡。
萧维桢看了眼被包扎好的伤口,下意识摸下脸,面具还在,昨夜的记忆恍恍惚惚,只记得他紧闭着眼,沉在水底,胸口愈来愈沉闷,耳畔的声音也模糊,如隔在世外。
他见伏案沉睡的纬彤,取过搭在床边的对襟羽缎斗篷披到纬彤肩上,瞥见微红的衣袖,轻揭开袖子,见她胳膊上一剜刀痕,纬彤夜里只顾着萧维桢,忘记自己在浴中故意割破的伤口。
萧维桢皱起了眉,自己挟持她,她却为自残以护自己,这笔债该如何偿还,却听见门外传来匆匆的脚步声,萧维桢谨慎地推开一丝窗户,透过缝隙,见院内已经被佩刀侍卫重重包围。
他朝后窗走去,叩门声响起,柔嘉唤着:“姐姐?姐姐?”
纬彤手心攥紧,这丫头不是那么好骗过去的,今早又来找麻烦!系好斗篷的猩红丝带,转身时与萧维桢四目相对,昨夜浴中的场景让她不禁红了脸,微蹙着挑了下眉,将脸别到一旁,拿过簪子狠狠地朝着伤口划去,刚结痂的伤口又被割破,鲜血涌流而出。
“你——”萧维桢一颤,不解地望着纬彤。
纬彤抽开他的剑,递给他:“你不要连累我。”
门被推开,地上一滩血迹,柔嘉见神情惶恐的纬彤被面具刺客用利剑挟持,长孙大人见站在门口迟疑的柔嘉,预想到事情不妙,踱步上前,大为失色,“来人!把箭给我!”他拉开弓,对准面具黑衣刺客,蓄势待发。
“爹!我怕!”纬彤抽泣着,对着长孙大人求救,欲要挣脱,剑在颈上抵出深红印记。
长孙大人满面担忧地望着纬彤,对着黑衣刺客说:“你莫要伤她!”
萧维桢挟持着纬彤,走到长孙大人面前,长孙大人见女儿莹莹的泪珠,无可奈何的退让到一旁,院内的侍卫纷纷拿着剑,纬彤痛苦地呻吟着,长孙大人摇头摆手,命令侍卫合剑,让路。
纬彤轻在萧维桢耳畔说道:“左走是马棚,快,骑马出城。”
:桃花梦
“出城后,一路向西,有个林子,进了林子,顺着水流走,有一个庙宇,绕过庙宇后是一片竹林。”纬彤对萧维桢说着,上辈子她因被诋毁命格与太子妃邦媛相冲,而罚到庙宇思过,夜间有群的盗匪闯入庙宇,她无意闯入竹林避难。
两个人骑马来到竹林,萧维桢抱纬彤下马,纬彤跑到竹林外,用脚踢着尘土,掩盖住血迹,对萧维桢说:“他们马上会追来,你快走吧。”
萧维桢扯下自己的衣服,拽过纬彤的手臂,试图帮她包扎,可却被纬彤推开,她对萧维桢说:“你见过帮人包扎伤口的刺客吗?”
纬彤拉过马,将马儿赶走,对萧维桢说:“你是谁,为谁效命,目的如何,我都不关心。但,你记住,我不是平白无故救你。”
萧维桢愈加不明白眼前的姑娘,纬彤淡然对他说:“我要你答应我,愿意为我无偿做三件事情。”
纬彤目不转睛的盯着萧维桢,她拿捏准了萧维桢重情重义的品性,知道他一定会答应自己,果然,萧维桢从怀里拿出一支竹笛,奏起一段乐音,递给纬彤。
“我吹奏起它,你就会出现?”纬彤接过笛子,旋转在指间,饶有兴趣地问萧维桢。
萧维桢点头,举起手掌,纬彤示意,与他击掌为誓。
“可我不会吹呀。”笛子在指间旋转,玉络飞舞。萧维桢从她手中夺过笛子,站在她身后,轻握住她的手,捏着手指按着音阶点着笛孔,重复了两遍,松开了手。
纬彤回忆着他的指法,尝试着吹起,随着微风,翠竹鸟语,萧维桢注视着她灵巧的手指,赞许的点头,看来的确是蕙质兰心。
“一直朝着林子尽头走,有条可下山的小路。”纬彤给萧维桢指路,萧维桢执手作揖,拜谢后,消失在竹林。
纬彤玩弄着笛子,欣赏着上面的雕花,一只栩栩如生的画眉鸟,林外传来喧嚣的人声,把笛子揣入怀中,躺靠在一支翠竹下,闭起眼睛。
“纬彤!纬彤!”
纬彤知道是萧炫,手被他攥得生疼,纬彤微睁眼,戴着束发玉冠,穿着玄衣白蟒箭袖,腕上缠着一串鶺鸰香念珠,目似点漆,用龙纹绣帕一点点轻拭着自己臂上伤口。
“太子殿下——”她反握住他的手,轻唤着他,随后无力晕倒在他怀中。
熟悉的荀令十里香方淡淡地包裹着她,丁香、檀香、甘松、零陵香,再取龙脑少许,用蜂蜜烧制,加入小茴香,她心中细数着每味香料,从前她把一寸相思全密密缝制在香囊中,萧炫却把自己推入烈火之上汹汹翻滚的蜂蜜中,融其骨,销其肉,断其胫,烧其心,炼化成一滴一滴的泪珠。
如今再闻这旧香,只剩下紧系在心肠上难消的恨。
“姐姐呢?”柔嘉在府中等着纬彤的音讯,见父亲归来,急忙问。
“被太子所救,直接去了太子府。”长孙大人捋着长须,回想起白日里的情景,太子殿下如此心系纬彤,这门婚事必须早日促成,朝廷中苏家的气焰快压过自己了。
在父亲走后,柔嘉不悦的掀翻茶盘,狠狠的念着:“长孙纬彤!”
萧炫一路快马加鞭赶回府中,对身后的小厮急命令道:“快去将军府,请维桢来府里。”
街市愈来愈繁华,人烟阜盛,不远处的街口蹲着两个大石狮子,萧炫侧身下马抱着她进了兽头大门,穿过垂花门,悬着画眉、雀鸟的游廊,转过金丝楠木镶大理石的插屏,来到正房,将她小心放到床上。
门外传来清朗笑声,“你刚回来就扰我的清幽梦。”
纬彤侧枕在石青引枕上,透过朦胧纱帐,打量着说话人,丈高八尺,青纱束发,脑后两个白玉珠环,身着磨银白衣战袍,腰系一条双搭桂枝玉带,手执一把折扇,心想着:“萧维桢打扮起来还算是人模人样。”
只见他拉开纱幔,俯下身,望着自己,转盼多情,天生的神韵全在眉宇,可惜让人难知他底细。
“姑娘,得罪了。”他笑着掂起纬彤的手腕,指腹搭在脉搏上,纬彤欲想把手抽回,她才不愿意再被这个人碰。
萧炫见纬彤不愿,劝道:“纬彤,这是维桢,虽是将军,但医术高明,你不信他,难道还信不过我吗?”
纬彤嫣然一笑说:“这位公子,我见过。”
纬彤的眼睛一直盯着萧维桢,想看他作何反应,可他却依然毫不在意,萧炫有些惊讶:“维桢常年在领兵在外,你们怎么会见过?”
纬彤执意坚定的重复:“我一定见过他,而且就在不久前!”
萧维桢打开扇子,轻摇着浅笑道:“我们是见过。”
“在哪儿?”萧炫追问。
纬彤饶有兴趣得望着他,只听他悠悠说道:“姑娘貌美,自是我梦中桃花仙。”
纬彤的脸如泼了朝夕般,瞬间红了起来,眉梢生了几分娇嗔的怒气,萧炫轻松释怀大笑起来,无奈地指着萧维桢说:“你呀!”
萧维桢卷起纬彤的衣袖,见到伤口时,纬彤见他眸中闪过一丝不忍,问:“怎么了?”
“见美玉受损,不免惋惜。”萧维桢仔细清理着伤口,落发滑落在鬓前。
纬彤婉转峨眉一笑:“并不是人人都像将军一样。”
他心不在焉的问:“一样什么?”全神贯注地用镊子沾着药水,轻点在伤口四处。
“怜香惜玉。”纬彤说罢,意味深长的看了眼萧维桢。
萧维桢的唇角上扬,望了眼狡诘似狐的纬彤,没有接她的话,转身对萧炫笑道:“并无大碍,只是姑娘接连几天受了惊,我开些安神的药,养几天就无妨了。”
萧炫悬着的心终于落下,安抚着纬彤:“你好些睡会儿,今天就留在我这里吧。长孙府一点也不太平。”
萧维桢坐在梨花木凳上悠然自得的泡着茶,屋内漂浮着特有的武夷岩韵。
“昨夜你上哪儿风流快活去了?”萧炫对萧维桢说。
纬彤盯着萧维桢,自己不揭穿他了,想看他会不会自露破绽。他轻摇着折扇,细品着茶,言语常笑:“桃花树下做了一场桃花梦。”
(点击”阅读原文”,查看后续精彩)
赞赏
转载请注明:http://www.dongyamedia.com/yzjg/1066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