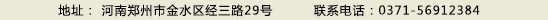那年夏末,关于猴子的生物实验彻底失败
人人都有故事,
这是[有故事的人]发表的第个故事
猴豫记(中篇节选.下篇)
?小杜
它们必须按照我们的时间安排怀孕——猴豫记·上「故事」
我忍不住琢磨,猴子是否也有灵魂——猴豫记·中「故事」
十、失败
冬越来越深。打过药剂K的母猴们腹部大了起来,一天一天不可逆转地大起来。我只好承认,整个临床预实验彻底失败,生物学实验上那种司空见惯、不清不楚的失败。
我用Nokia把这失败告诉老大。他在千里之外的东北说:
"行,我知道了。收拾收拾回来过年。别忘把账给我整明白了,发票带上。"
因这倒霉的欲实验,我在国道边与猴子厮混大半年,小屋的墙上用砖头蹭满了"正"字,到头来只是老大这干巴巴的一句。可猴子们却又盼来什么呢?
老大和赵场长在电话里谈妥,母猴连同刚生的小猴崽全部归猴场所有。
我紧握锈迹斑斑的铁栅栏,仿佛看到这些母猴齐刷刷地做了娘,独臂杨过数天内接连当了几十只猴崽的爹,却依旧在自己的小屋踱来踱去,胸前荡着仅有的那支猴爪。依据市场行情,这些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或去广东被灌醉敲开脑袋,或卖给村里的耍猴人四海为家。决定猴子们命运的是日本人开发出的药剂K,是国家课题基金,是赵场长,是广东人,是我们老大--东北某省医学院的系主任--还有我这个满脑袋鲍勃迪伦大门乐队的家伙。
赵场长兴高采烈地在猴场前后来回走动。他仿佛看见无数个小猴崽子吱吱乱叫满天蹿飞,而他的猴场则像母猴肚子那样越鼓越大。
"你们这药避个鸡娃子孕,当成保胎药卖给咱村儿算毬了!"
赵场长撇下这句话,跨上越野摩托。夕阳下,国道边,他身影越来越小,好似一只飞向天边的蝙蝠。
我洗了一根黄瓜,向杨过的铁栅栏里递去。我在河南递给猴子们的最后一根黄瓜。要说这杨过交配了场里的所有母猴,注定要成为数十只小猴的爹。从动物社会学的角度来讲,它才是这猴场不折不扣的王者。可面对这根冬日里的黄瓜,它却诚惶诚恐,迟迟不肯伸出那只单在胸前的手臂。
其实也难怪,刚入冬那阵,我曾把半截黄瓜递给杨过,作为它在母猴身上弹无虚发的奖励。杨少侠从母猴背上跳下来,怪叫一声,接过黄瓜就啃。我转身拿起地上那根冲过萧峰的黑管子,往杨过身上冲水。这独臂猴登时就被顶了个跟头,灰溜溜钻回角落;倒是刚刚和它爱过一回的母猴向我呲牙咧嘴。以后杨过远远见我穿大头鞋走来,就越发地怕了,窝在角落,那支独臂护在胸前。对面猴圈的萧峰依旧面无表情。
我叹了口气,把黄瓜塞进铁栅栏的窄缝。小张拍拍我,你要走吧,咱俩再喝一顿散毬了。
还是村头小铺里的黄酒,刀鱼则是正儿八经南阳城的货,可不是赵场长用猴粪喂出的虾兵蟹将。我问那你以后咋办。小张说他也快要走了,兽医专业一毕业就跟小对象结婚。他还说"赵场长还挺毬够意思",多给了他一千块奖金。我听着一哆嗦,寻思这钱不会来自广东人下的猴子订单吧。但一想小张好歹也算哥儿们,便猛灌两大口黄酒,心下也就飘飘忽而释其然了。
可这位在河南交下的哥儿们,现在连模样都记不大清,顶多是细细的小眼,乱蓬蓬的卷发,纯粹一卡通形象。倒是那些毛脸赤腮的猴子,让我念念不忘,唠叨至今。
十一、刀削般的小腹
二十岁这年夏末,我住在一个小屋,河南省国道边上。经常失眠。每到夜深人静,我默默躺在床上,一边看窗外扫过的车灯,一边听潮水般涨落的马达声。
心里难免会想:刚才过去的那辆是什么车?车里坐了什么人?那人在经过我窗前的那一瞬又在想些什么?
我住的这小屋很简陋,几乎是一个棉花地边上垒起的小水泥盒子,把我和后面那群猴子隔开。睡觉在这小盒,烧饭也在小盒。也正是因为它,才让我觉得在天地间总算有了点依存。后来,我回省城医大躺在宿舍的床铺上,一闭眼还是国道边的那个小盒子。
在医学院我经常锻炼身体。那时迷上了克林伊斯特伍德--那个在无数西部片里扮演孤单英雄的老家伙。在医学院门口的地摊上,我看到一本叫《廊桥遗梦》的小册子,封面上是克林伊斯特伍德和他那顶破烂牛仔帽。我买下这小册子,捧回宿舍脱头脱脑读下去,居然发现是一本描写中年女人婚外情的小说。我把册子从里到外翻个遍,也没发现它跟克林伊斯特伍德有什么关系。然而那中年女人对男主角的第一眼,我却牢记在心:
"刀削般的小腹。"
我当时躺在宿舍铺上,一边掂量这句话的分量,一边摸了摸自己的小腹。同寝几个家伙有人泡面,有人洗袜子,有人嘟嘟囔囔背单词。我莫名其妙心生厌恶,打开窗子,把《廊桥遗梦》撇了出去。我决心要让自己和这几个家伙不一样。先从身体上做起。我要把自己的腹部变得像刀削一样。
这便是二十岁的我,一个妄图用大块胸肌证明自己与众不同的小伙子,一个留长发穿大门乐队T恤就和整个世界格格不入的家伙。
我当时那心思出奇的简单,一有什么想法,不论多荒谬可笑,马上就身体力行。我训练自己身体的项目只有三项:俯卧撑,单杠,踢球。俯卧撑主要锻炼臂膀肌肉,实施起来快捷简单。单杠就对整个上半身要求都很高,尤其是腰腹。至于踢球,除了练习跑动和身体协调性之外,亦是个人爱好所在,乐此不疲。要说二十岁的身体,锻炼起来真的见效很快。后来认识了单身母亲,她就总爱用手指捏我身上的"几硬坨肉"。我则把《廊桥遗梦》里那句"刀削般的小腹"当成笑话讲给她听。
可是到了河南,停止锻炼,不到一个月我就发现自己开始虚胖。我每周进南阳城洗一次澡,每周都会对着洗浴中心的大镜子心惊肉跳。除我之外,那镜子里还晃动着几个白花花大腹便便的男性躯体。他们身上的肥肉随着脚步发颤,他们却对此熟视无睹。我觉得可怕。生理课上我曾抄过"伴随年龄增长,新陈代谢速度不断减缓,脂肪沉积则明显加快"之类的笔记。我知道这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宿命,可二十岁的我想尽力抗拒它。我不想变成个胖子回东北见单身母亲。在河南我谁都不认识,过着囚犯般的日子。头发可以不理,胡子可以不刮,但我要把身体变成东北时的健硕。
俯卧撑是最先恢复的项目。屋子里因烧火做饭,地上很脏,我就趴在床上做。边做边对着墙上那些砖头蹭出来的"正"字喘粗气。我想起了监狱里的囚徒:谁最肯锻炼身体,谁就最想重获自由。
若小张或赵场长不在,我也会跑猴场做它一气。我站起来拍拍手,看着周围没精打采的猴子,心想:它们原来在山野里自由自在,会是怎样的运动量?那时的体态又是怎样?被关这么久,它们是否也会像人那样长出浑身发颤的肥肉?
然而这毕竟只是个小村子,没有单杠,没有球场,有的只是一条无尽无止的国道。我只好退而求其次,把单杠和足球合而为一,改成跑步。开跑之前,我特意去了趟南阳城。乱逛一天,遍寻不见运动短衣短裤,反倒在地摊上买了一双"男人王运动鞋",底下是两排黑色的胶皮疙瘩,让我想起中学时穿的那种回力球鞋;盒上则印着罗纳尔多那张肥硕的脸。回村我又翻出迷彩裤,膝盖往下齐刷刷地剪掉,当成短裤我套上,还有大门乐队主唱的白棉T恤,再配上新买的"男人王运动鞋",便撒腿往国道上跑去。
村里的老乡都看呆了。他们实在没法理解眼前这个甩着长发一路狂奔的家伙。可村里的孩子们却很欢乐,他们跟在我身后跑了起来,连同两条闲极无聊的野狗。
我可管不了村人怎么看我。我在这儿呆了半年,变得跟猴子差不多,我还管人类怎么看我?我继续发足狂奔,把孩子们还有野狗都甩在后面。我大口大口喘着气,腿部在颤抖炽热,那一定是脂肪在燃烧。我从心底里感到快乐。最原始最有力的快乐,永远来自身体,永远来自感官。
我大步向前跑着,广东人开着他的重型长途大卡从身后呼啸而过,转眼消失在田野尽头的暮霭,一百二十迈的速度把我眼前的三维世界压缩成了二维。
国道左侧是棉花地。大片大片浮动着的棉朵,就像落在田野里的白云。可是一过十月,棉朵就都被摘掉了,只剩黄秃秃的枝叶。再过不了多久,秋雨连浇带泡,连那些枝叶都成了泥土的一部分,整片田野在我眼中就只剩下灰色。
国道右侧是小张天天往里填猴粪的的养鱼池。秋风微起,若从远处望去,这池子也会波光粼粼。到了冬天,漫天大雪会把大地连同池子一起覆盖。可是中原的雪注定要在二十四小时之内融化。尤其是落池上的雪,迅速被底下黑色的池水吞掉;再和旁边仍是白皑皑的大地一衬,就像巨大的墨汁滴到无垠的白纸上。冬天最冷的时候,这池子也会上冻,颇妨碍赵场长捕鱼。这个老流氓会用镐头在冰上面刨一个窟窿,把雷管丢进去。轰一声巨响,池子被炸开,云里雾里的鱼们、还有已化为淤泥的猴粪从天而降……你瞧,在雪里我跑的有多慢,这才刚刚过了养鱼池。
距离村子四五里远的国道上,有一个不为人察觉的岔口。顺着那岔口一直往前跑,就会看到一个镇子。过去我曾骑着三轮车去那镇里买菜买肉,或是洗澡。每次都在周末,就为了赶上那镇子的集市。
这集市其实跟我在东北老家见过的差不多,就是各种农副产品、还有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一个热热闹闹的大party。唯一不同的是河南这集市上会有几条大狗在游荡,体型夸张,差不多有小牛犊子那么大。它们抽动着能塞进拳头的鼻孔,慢悠悠地搜寻吞咽肉摊弃落的猪肥膘。我一开始很怕这些巨狗,时间久了竟发现它们愚的很。抡起大头鞋踢它一脚,那巨狗顶多只懒懒回头看你一眼罢了。
不过我跑步进了镇子,却不见任何集市。满满一街的人,满满一街的鸡零杂碎,满满一街的叫卖吆喝,还有那几条莫名其妙的巨狗,全都不见了。他们就像约好了一起变戏法似的,每到周末就呼啦一下不知从何处冒了出来。
其实当我跑到镇子的时候,也是精疲力尽的时候。集市那条街的尽头,便是我的终点。阴风呼号,没有半个人影。我一个人站在那里,大口喘着粗气,一边体味有氧运动过后那种深入骨髓的快感,一边想象这里到了周末就又是满满一条街的热闹喧腾。我分辨不清哪个是真,哪个是假。
岂知雪越下越频,那双"男人王运动鞋"也脱了帮子,我没法再跑下去,只好找根麻绳,准备在猴场中间的空地上练跳绳。可是麻绳太漂,根本悠不起来;我就在当中缠了几条细铁丝。这下好了,一悠起来呼呼生风。我小时跳绳很差,跳的慢不说,那些拧麻花之类的花活更是一窍不通。可是在河南因为有了大把大把的时间,我居然越跳越快,甚至练起了小时不敢染指的花活。我风雪无阻地跳着,缠绕着铁丝的麻绳都把地上的雪和泥都刮没了,露出一道浅浅的坑来。我刚开始跳的时候周围猴子还会用猴爪捧着铁栅栏凑过来看看,那景光实在跟人类看耍猴子相差无几。可日子一久,不论我再跳什么花活,猴子们也都懒得理我,纷纷回到墙角,继续抓它们的虱子,晒它们冬日里弥足珍贵的太阳。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果然恢复了在东北时的健硕。对着南阳城洗浴中心的镜子,我看见自己原本鼓起的脸颊重又凹陷下去。我本该高兴才对,可心里却泛起了悲哀:我把身体练成这样到底为了给谁看?给单身母亲看?给猴子们看?给我自己看?
我坐末班大巴回到国道旁的小屋,墙角里躺着那本被遗落的台历。头几页已经缺失,所以我都没法弄清所指的年份。我拂了拂积下的灰尘,打算用它来写几页日记。
那台历每一页都分正反。正面都是红字,大号字体是阳历的月份阳历的日子,小号字体是阴历的月份阴历的日子,下面还注明节气节日之类,还有些"冲龙煞北,宜远足,忌婚丧"之类不知所云的文字。反面都是黑体字,"芹菜在下油锅之前可否用热水焯",那种谁都不会在意的生活小百科小常识。最匪夷所思的是我翻到七月份,居然读到了一段半荤不素的夫妻间的小笑话。
我在印有红色字体的正面开始写日记。或者只是随便涂涂罢了。比如说抄上当天给单身母亲发的所有短信那些石沉大海的短信,再起一个题目,"为了忘却的纪念"。比如说记下当天给单身母亲打电话是几时几分,她是关机还是未接,彩铃音又换了那首歌等等。有时我干脆把赵场长连同月经不调的母猴子们恶狠狠地诅咒一番,或者抄几句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
偶尔,我还试图写下这样的句子:
"当鲁滨逊先生摘下他亲手栽种的第一个西红柿,他感到一阵莫名的绝望。实际上,这意味着在这四面环海、热带季风终年拂过的无名小岛,这种红色多汁的果实会伴随他固老终穷。鲁滨逊先生简直是在给自己种植一株妖艳无比的殉葬品。最要命的是,直到黑人星期五的出现,他的这种悲观情绪也没有丝毫衰减。"
类似这样的句子还有几个,基本都是我在国道跑步时偶尔想到。就像你猛一抬头,天上正默默飘过一排大雁。
其实,更多的时候,我只是抄起那半截砖头,再往墙上添一道红的,便又多出一个歪歪斜斜的"正"字。这其实跟在日历纸上乱涂差不多。
十二、夜戏
因为我们这个猴子实验,赵场长这年本来赚了不少,可谁知年底他的母亲去世了。我行李都打好包了,本以为扛着就回了东北,可还有猴子上的账务须和赵场长结算,只好再捱几日,等这场丧事完毕。
此前我在村里见过赵场长的母亲。瘦高瘦高的一位老人,无论什么季节,头上罩一白色帽子,双臂戴深蓝色套袖。
人们都说,老人若生的富态,看起来会慈祥。这赵老太刚好相反,走起路来大步流星,脸因削瘦而显得沉郁,即使在笑也好像心事重重。村里的孩子都躲她。
可刚一入冬,老人竟去世了。脑溢血。走的突然,安静,只留下三个赵姓男人:儿子赵场长;两个老赵头,一位是多年前棉花地里的情人,另一位是过了大半辈子的老伴。
按村里规矩,长辈过世,晚辈要哭嚎,要摆酒,还得请人唱戏。赵场长天天为猴场生意东跑西颠,一天出入南阳城数趟;尽管亲娘没了,但要让他哭嚎根本不现实。反过来,倘没眼泪,他本人大概也不屑在村人面前装哭。
换成别的赵姓男人,自己哭不出还可以让老婆孩子替着哭。可我们赵场长偏偏又是个孑然一身的光棍。好在他不缺钱,干脆请来一支白衣白帽的哭丧队,两女一男外加一个娃娃。
但这哭丧队不算职业。尤其是那男人,嚎出来的嗓音像鸭叫。更糟的是他那脸好像还涂了一层铅灰色的粉,阳光一晃难看极了。两个女人,照我看有个还长的不错。我偷偷问了问小张。他也觉得那女的不错。而那个娃娃--大概因入行没多久--是这哭丧队里最卖力气最不偷懒的。他们在村里来回绕了两三遍,这娃娃一路干嚎,最后落棺还流了眼泪下来。村里的孩子们都站在路两旁,看着这个出来混江湖的同龄人。
哭完丧便是摆酒,最为赵场长所擅。村里没有酒楼饭店,二十来桌丧酒便摆在猴场。正面大门口坐的都是上了辈分的老人,连带几个有头有脸的男人。赵场长便坐此陪酒。猴场后头那块空地--就是我和小张平时给猴子配食料的地方--坐的都是孩子和媳妇们。或许因为我是研究生,我一开始被安排在了前面正席。可村里几个爷儿们发现我酒量忒差,又不会划他们那个花拳,就觉得没意思,不再理我。至于赵场长,早已摘下脑门那顶白纸糊的高尖帽子,大口大口喝酒,胸前那片丧服早被打湿了。
我偷偷溜去猴场后头。那里可真是欢乐。媳妇们筷子夹了花生逗铁栅栏后面的猴子,孩子们就干脆把黄酒倒进猴子喝水用的小铁盆。傻乎乎的虚竹那天很是开心,一边往嘴里塞着藕块,一边揪自己脑顶最后那几根毛。
我还瞧见那支小型哭丧队,单独一桌,有肉有菜,却没有酒,四口人一声不响站那儿吃。那男的自己管自己,脸上的铅灰色已被抹掉大半,露出白化病的斑痕。两个女人倒是轮流给娃娃夹菜,我没弄明白到底谁是那孩子亲娘。
按规矩每桌都应摆酒,唯独哭丧队没有。我就问小张为啥。这小子皱眉说,他们吃哭嚎这碗饭,怕喝酒坏了嗓子。
小张这话大概不错,因为丧酒摆完这哭丧队还得继续干活。这回再哭就不是在村里哭了,这回是要哭到镇子上去的。就是我时常跑步去的那个镇子。吃完肉,他们哭的更卖力,尽管没有眼泪。在村里哭还有那么点给死人哭的意思,到了镇里那根本就是哭给活人的,哭给赵场长的钞票。
赵场长不但请了哭丧队,还在镇里搭起台子,从南阳城里请来戏班。赵湖村的男女老少浩浩荡荡往镇里看戏。每个人都酒足饭饱,每个人脸上都红呼呼的。要不是哭丧队在前面干嚎打头阵,你说这是一支娶亲队估计也有人信。我那天喝了不少酒,跟着队伍晕乎乎地走着,看着国道两边的景致,心里有点糊涂:昨天我还在这上面跑步来着。
镇子这条主街我很熟悉,无论是集市还是空荡的时候。戏台就摆在主街当中,木架拼凑,能拆能搬。哪里有红白喜事,哪里就有这戏台;哪里有这戏台,哪里就有婚丧嫁娶人间悲喜。
戏台对面已摆好长椅。每条长椅旁设一个暖壶,一摞瓷碗,一盆瓜子。媳妇们领着孩子说说笑笑抓了瓜子再入座。喝过酒的赵姓男人们却矜持肃穆,顶多是倒碗热水喝罢了。赵场长踉踉跄跄于戏台和长椅之间,既要跟各路领导点头哈腰,又得找人点钱打发哭丧队走人。亲娘去世,他喝了不少酒,团团乱转;亏得他平时应酬多,不然真未必吃得消。
赵湖村的人都在长椅上坐定。又过来不少镇上来的人,都是凑热闹的。台上终于有人发话。这人既不唱戏,也不敲锣,他是南阳市来的领导。
市领导颇讲了几句,大意是老太太功德无量,养育了赵场长这么一出息儿子,于家于国贡献不小,云云。
领导讲毕,赵场长鞠躬,众人鼓掌。领导挥挥手,台下把赵场长拽到一个角落,手握手又说了半天话,才钻进轿车,沿着国道,回了他的南阳城。
领导走远,戏班子才出来开唱。可惜都是河南梆子,我一句听不懂。问小张唱的是啥,他抬头茫然四顾一番,又埋头发他的爱情短信。我只好专心去看台上这位穿了戏裙的演员。我双眼紧跟着她那双来回甩动的袖子,刚开始还拿不准她到底是不是女的,因为印象中戏曲里动不动就让男人来装女人。
台上乒乒锵锵,台下的我脑海里居然回荡着大门乐队。
日头渐渐斜了下去。我听得困乏,周围赵湖村的男人们或歪脖打盹,或正襟危坐。女人或交头接耳,或磕着瓜子。孩子们就早都跑光了。可戏台上的班子却依旧卖力。那女演员还是不停地甩着袖子,敲锣打鼓拉弦的几位也都翘着二郎腿,自顾自地摇头晃脑。嘿,这要换成大门乐队的演唱会现场,眼前这哥儿仨不就是吉他贝斯键盘手么?
天已黑透。女演员收了她的袖子,我听不懂的河南梆子总算收住。本以为这就散场拉倒,却被告知还有个午夜场。
村里人说,这戏须要唱到天亮,死人听了才会安心地离开此间。按这说法,赵老太的亡灵肯定就坐在戏台下的某条长椅上,和大伙一起听这出热热闹闹的河南梆子。
我试着想象我前面的那条长椅,上面坐了瘦高瘦高的赵老太,头上是她的白帽,胳膊上是她的深蓝套袖,正和媳妇们一起磕瓜子,聊闲话。此地悲怅,不在别处,就在大碗大碗的黄酒,在散落一地的瓜子皮,在直入夜空的梆子戏。
瓜子嗑了一地,暖壶里的水也凉了。不少人都起来去戏台后面解手。刚才在戏台上甩袖子的女演员披了军用棉大衣,独自坐在角落,手里捧了一大碗热茶。
人又走了不少。稀稀落落的,比天上的星星还寥落。戏台的大灯亮了,光圈下站着一个男人,看起来像是位丑角。他细着嗓子说,对不起乡亲们,今晚人走这么多,一半是他们团当家花旦唱的不好,一半是因为他本人实在太困,鼓点总是敲错。台底下就笑。
他也跟着笑。笑完了又说,当家花旦就只能唱到这份上了,但是他却可以不困。
咋个不困?抽支烟就不困了。
台下就有人起哄,撇了一支烟上去。他叼在嘴里,说莫带火。台下又丢了打火机上去。他把当家花旦--就是刚才甩袖子那女演员--叫上来,让她面对大伙,撅嘴把烟夹住。这丑角喊道,大家注意了,我点烟可根别人不一样,只有我这样点着的烟半夜抽起来才不困。
我总算来了点精神,拽拽小张。我俩眼睁睁地看着那丑角把嘴凑向女演员涂了胭脂的脸颊,叼住香烟;又将手伸向当家花旦另一侧脸颊,火机点着烟,转过来笑嘻嘻地抽着。台下一片叫好。丑角叼烟鞠几个躬就下去了。当家花旦又咿咿呀呀地甩起了她的长袖。
台下却更为稀落,暖壶碰翻两个,瓜子也再没人嗑了。那戏词和锣鼓兜兜转转,飘散开来,倒好像是专门唱给这冬夜似的。
戏又停了。丑角又出来给台下振作精神。他说这回他也没法了,只好请孙大圣过来帮忙。当地一声金锣,就跳出来只猴子。台下几个人还是昏昏欲睡。我见是猴子,总算来了点精神。但见那丑角向猴子伸出一条木棒,唱道:
"大圣,拿好你的如意金箍棒!"
猴子却一摆手,不接那木棒。丑角却非要给猴子木棒。推来搡去,丑角就用木棒打了猴子一下。猴子生气,一下子窜到木棒上头,甩了那丑角一巴掌。台下勉强叫了几声好,丑角收起架势,摁着猴子脑袋给众人鞠躬,就都下去了;又换成当家花旦上台来甩袖子。昏暗中只能从身形辨出是公猴,根本看不清那张毛茸茸的猴脸儿,也不知是不是我们猴场养出来的。
长椅上都没什么人了。媳妇们早已回村,只剩下几个男人。最前排躺着的是赵场长。自从把市领导他送走后就躺下睡了,根本没听自己请来的梆子戏。赵场长两侧是正襟危坐的两位老人,一个是赵场长的亲爹,一个是赵场长的养父。
关于这赵场长的身世,在小小的赵湖村里流传着无数版本。有人说赵场长是当年他亲爹和赵老太在棉花地里野合出来的,有人说赵场长的养父真是个糊涂蛋,居然替别人白养个儿子。小张却告诉我:养也不算白养,反正他们爷儿仨全姓赵,分那么清有个毬用。
风言风语的固然不好入耳,可赵场长却满不在乎,因为这丝毫不能改变他在赵湖村的地位。他甚至把两位赵姓老爹都请到猴场帮忙,自己就专心骑着他的越野摩托,去南阳市里拜见领导,去国道边的下流酒馆买醉。
如今赵老太去世,赵场长不胜酒力,睡在了戏台前的长椅上。母亲的亡灵假若真的就坐台下听戏,恐怕也不会怪责儿子。两位当年颇有番恩怨的赵老爹,却都一直端坐在长椅上。一个有过一段情,一个过了一辈子,我很想知道是夜赵老太的亡灵会坐在谁的身边。
Nokia终于让小张摆弄没电了。我俩走国道回村。那夜并没有什么风,但我仍能依稀听见那当家花旦唱的河南梆子。
没有星星,没有月亮,夜空黑不见底。等这夜被黎明破了,梆子戏也就唱完了,赵老太才算放心地告别了这赵湖村,告别了她酒醉的儿子,告别了两位正襟危坐的赵老爹,告别了她生命中这三个姓赵的男人。
至于我们赵场长,他酒醒后第一件事是红肿着眼睛胳膊上戴孝,第二件事就是找我清算结余的猴账。总之他重又跨上他的越野摩托,为他的猴场事业奔波。
而我总算扛起行李,回我的东北。
十三、新年
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反正回东北前我把头发剪了,在南阳市中心的理发店。看店的是位大嗓门儿的东北姑娘。她说她过年不回东北。对象是南阳市里的,今年春节对象家过。
我问她想不想咱东北。
"咋不想呢,这疙瘩过年老没意思了,饺子都没酸菜馅儿的。"
我低头盯着地上,落下的头发越来越多,那姑娘在我脖颈上的鼻息。
我掏出直板Nokia,给单身母亲发了短信:
"我把头发剪了。"
没有回信。
那姑娘的手停在了我的脸颊上:
"剪完了哥,抬头看看咋样。"
镜子里那张学生模样的脸,正茫然无措地看着我。
跟来河南时一样,我还是坐棺材般狭窄的硬卧回了省城。医学院人都走光了。只好叫了几个家住省城的哥儿们出来喝酒。烧刀子,涮白肉,宿醉,头疼欲裂。
我独自一人躺在学校宿舍的床铺上,掏出那张回家过年的火车票。粉红色,硬座,巴掌大小的小纸片,一端是省城始发站,一端是县城终点站,夹在其间的将是整整一夜的嘈杂、拥挤和污浊。
上车前洗个澡吧。我从铺上爬起来,揣好车票,扛着行李,去了学校的公共浴池。
浴池里只剩一个看门兼搓澡的中年男人,还有断断续续的滴水声。那男人身上皱皱巴巴的,被浴池里的水汽泡个惨白。一对经年累给人搓澡的臂膀,倒是青筋暴跳,安放在这样一副躯干上,让人说不出的厌恶。
他搭着浴巾,探身进来,问要不要搓澡。我干脆地回绝了。
热水剩的不多了,似乎给每个莲蓬头匀了一些。所以每冲一小会儿,我就只好换一个莲蓬头。换到紧靠窗子的时候,温水滴在了我后背的伤疤上。
那块疤可能来自初中时的一次群架,也可能来自球场上的一次飞铲。都已经不重要了。我甚至连那疤长什么样都不知道。我只觉得温水滴落的时候微微发痒。
又换到下一个莲蓬头。水流还算大,我闭上了眼睛。
单身母亲小腹右侧上的那条疤痕清晰可见。当时她难产。她怕疼,就选了剖腹产。柳叶般的手术刀在她的小腹上划过,像打开拉链一样,取出了一个满是血痕的新生命。
这生命长到三岁那年,我抚摸着她母亲的小腹,低头轻轻吻了一下那条粉红色的疤痕。
我睁开眼睛,在莲蓬头下胡乱冲了会儿,就擦干身子,换上干净衣裤。那个男人正歪在长凳上抽烟,阳具垂头丧气地从浴巾下面耷拉出来。我抽的是哈德门,很呛很冲,单身母亲家仓买的烟里最便宜那种,我过去经常去买。
有段日子没抽了,我向这男人要了一支点上。又掏出直板Nokia,给单身母亲发条短信,说我人回省城了,挺想她,也报个平安。依旧没有回复,至少在那支哈德门抽完之前。本来要打个电话过去,可拨键时却发现自己都记不清这女人的模样,当下变了主意,一下就把她的号码给删了。
我扛了行李,走出浴池,往外呼着东北深冬特有的白气。回家那趟车始发站很小,就在校围墙外侧。非典那年春天封校禁酒,大伙开玩笑似地在那墙上开了个豁口。某个皓月当空的夜晚,我曾在这豁口帮单身母亲搬了好多箱啤酒。眼下我吹着口哨,大步跨过那豁口。在河南养猴子穿的迷彩服早扔了。那件大门乐队的棉T恤倒还留着,团巴团巴塞肩上的行李包。
虽然明天就是大年三十,但始发站人还不多,我邻座就是空的。我把行李放了上去。对面是一对夫妇,大包小包的,估计也是回老家去过年。
火车就像一条长长的磁铁,不停地吸附着天南海北互不相干的人们。一进了省城中心的大站,人更是骤多。攒动的脑袋和胳膊,夹裹着各式各样的行李,时而向前,时而阻塞,成了一条粘滞无比的河流。人在里面就像是一条条拼命游却游不动的鱼。
一个老人挤到了邻座。我起身把自己行李放到了架子上。
这老人也是疲惫了。行李架其实还很空,她却只能把包裹放在座位之间的小桌上,一只枯老的手搭在了包裹上面,另一只手则捂着胸口。
对面的中年夫妇试图跟这位老人搭话,但她却缄默不语。
火车跑出省城,把城市的灯火甩在后面,窗外就只剩漫无边际的黝黑,看不出是白雪覆盖的原野,还是被冻硬了的大江。至少还不算吵。在赵湖村跟猴子们呆了半年,我早已习惯不插耳塞,今夜不插电也不弄弦。有没有鲍勃迪伦大门乐队其实都无所谓。我合上双眼开始睡觉。
不知多久被推醒了。是个小伙子,和我年纪相若。他说他想和他母亲坐在一起,但车票位置买错了。
我从架子上取下行李,和那小伙子一前一后,穿过无法穿过的过道,来到另一节车厢。
我坐了下来,邻座和对面居然都是姑娘。有点意思,不要姑娘要亲娘。我回头看了一眼那换座位的哥儿们,他那背影已隐没在过道。
一共有三位姑娘,我来了兴致,睡意全无,把塞满脏衣服的行李扔到桌下,和她们一边打扑克牌,一边聊天。很快就发现其中有一姑娘居然还是校友。我们大声说笑,好像这里不是拥挤肮脏的车厢。
我听过嗓音为酒精毒品蚀害的鲍勃迪伦,我读过《朝花夕拾》《且听风吟》,从专业课上学过像毓婷这种小玩意儿究竟怎样干掉一个胚胎,在河南的棉花地看了半年猴子的大姨妈,所以我颇攒下几个令人哭笑不得的小段子。姑娘们被逗坏了,气氛越来越热烈。
"在村儿里我头发留到肩膀那么长,还带卷,染黄了就跟你手里那张J差不多。"
我讲得口干舌燥。那位女校友递过来半瓶矿泉水。我一口气喝掉。心里没那么燥了,就跟着想起那几张毛茸茸的猴脸,一阵难受,就一个人去了吸烟区,想让冷风吹一吹。
所谓吸烟区,无非就是两节车厢之间的连接通道。车轮每碾过一节铁轨,在车厢里只是微微一荡,到这里却成了实实在在的摇晃。没有任何取暖设备,任由原野的寒风穿梭。饶是如此,昏暗的通道上还是东倒西歪了几个穿棉大衣的人。
我边抽烟边打量这几个蜷缩在硕大行李包上的人,很难理解他们如何沦落于此挨冻受罪。
在这半明半暗中居然有个人站了起来,张口说要烟。我吓了一跳,丢下手里那包烟和简易打火机,慌忙回了车厢。
我挤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从连接通道上带来的寒气,已蒸腾在闷热发涨的车厢里。我继续和姑娘们说笑。到了后半夜,她们实在支持不住,都伏在小桌上睡觉。我起身去上厕所,门口排队时往吸烟区的连接通道那边瞄了一眼,好像真有几处烟星在闪烁。
再回到座位,姑娘们已睡的沉了,小桌上满是她们黑黑的长发。我靠在椅上,再次合上双眼。
醒来时,我发现自己斜靠在一个人的腰上。那是一位矮个子的中年男人,正伏在我背后的靠椅上打盹。我推醒了这中年男人,让他坐到我的位置。
中年男人却摇摇头,微笑说他马上就到站了,到家了。
对面那位校友姑娘也醒了,正对着车窗哈气。本来被冰霜盖住的车窗,现出了圆圆的一小块鱼肚白。她掏出手机,先是发短信,又打电话,想是告诉爸妈或男友:我快到站了,到家了。
另两位姑娘也醒了。从她们脸上的细节,我意识到这一夜自己脸上大概也全是汗和油。
和其他人一样,姑娘们也开始忙碌起来。发短信,打电话,排队洗漱,排队上厕所。
我家县城在终点站,所以不着急。手捂着下巴,看着姑娘们在车厢里忙前跑后。
黎明的到来,让车厢陷入欢快。虽说一夜疲惫,但毕竟是要回家过年了。三个女生临下车之前还请我吃东西。那位校友姑娘甚至递过来一张保湿面巾纸。我擦了擦脸,把这一夜的汗尘与油垢留给了面巾纸。我祝她们新年快乐。她们高高兴兴地下车,走了,回家了。
又是一个大站。火车停下多久,车厢里的吵闹就有多久。待到重新安静下来,便只剩下车轮碾过铁轨时的微微一荡。
我扫了一眼车厢,就剩下两三个人,都把腿放在对面的椅子上闭目养神。我起身去了吸烟区的连接通道。空空如也,昨夜那几个穿棉大衣的人已经不见了,只剩地上几根烟蒂。
我回了车厢。乘务员开始为进终点站清洁打扫。橘皮,香蕉皮,饼干渣,红肠衣,瓜子皮,还有残余汤汁的碗面。睡眼惺忪的乘务员骂骂咧咧,她实在有太多理由抱怨不满。然而这些乱糟糟的垃圾,却是关于这车厢一夜的唯一记录。
服务员把黑色的垃圾袋大张开口,伸了过来。我将那张揉搓的不成样子的面巾纸团成团,丢了进去。我转向车窗,女校友留下的那一小块圆圆的鱼肚白又被冰霜盖住了。
我捧着自己的行李包,对车窗大口哈着气,很快又现出了一小块透明。从那块圆圆的透明,我窥见没有一朵白云的蓝天,缀着几堆残雪的田野,我窥见只差一个白天就来到的新年。
抗癌药物研发小杜有故事的人本文责编:糖糖
版权为有故事的人所有,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人人都有故事
一个献给所有人的故事发表与分享平台
转载请注明:http://www.dongyamedia.com/yzjg/1079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