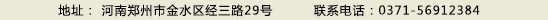崔亚伟陆佰的菜窖
点击上方"同步悦读"免费订阅
力匕
陆佰的菜窖■崔亚伟
阝勹
廴匚
陆佰死了,像飘落在泥土地上的一片雪花,瞬时消融了,没有声响,没有色彩。陆佰的真实官名叫什么,村里没有人知道。我一直就叫他陆佰大爷,于是很长时间,我以为陆佰肯定是姓陆。有时候也叫他大爷,把前面的“陆佰”省略,这样好像显得亲切些。
陆佰在我出生前好多年,就来到我们村了,准确地说是下放我们村的,然后和我家就成了邻居。当然,所有这些都是从我父母那里,支离破碎地随便听来的。有时吃罢饭闲扯,父母谈论关于陆佰的往事。从他们惋惜的表情,我渐渐猜出很多关于陆佰的过往信息。例如,陆佰要是不被下放,到老也就吃上老保了,现在却成了村里的光棍。我好奇地问,陆佰原来没有媳妇吗?为啥让人家下放?母亲就呵斥我,小孩子懂什么,瞎问啥。父亲也开始吓唬我,你要是不好好学习,将来和陆佰一样打光棍,好好学习,咱以后就吃香的,喝辣的。
我对陆佰的鲜活记忆是从他家的菜窖开始的。那是一个很大的拱形菜窖,在地下四五米。陆佰的菜窖比我家的大多了,我家的只有他的五分之一,大概在全村也是最大的。
与其说是菜窖,倒不如说是地下房间。
酷暑放假,我最喜欢钻进陆佰的菜窖。他好像也欢迎我去他的菜窖。陆佰掀开菜窖洞口的木盖板儿,说,进去吧。我把双手撑到窖洞沿上,托起身子,双腿探下去,岔开,脚踩到窖洞壁上的踏孔里,手脚交替地蹬着踏孔下到菜窖里,瞬时浑身清凉。陆佰也跳了下来,伸手从窖壁上一摸,咔咔两声脆响,菜窖里就猛地亮了起来。拱形的窖顶上吊下一个灯泡,发出暗红色的光。窖壁是青砖砌成的,遇到灯光后反射,显得有点儿黄。左边放着一张单人木床,铺着黑乎乎的被褥。右边靠墙一张四个抽屉的长条桌,一把木椅子。桌子上面墙壁砖缝里塞着个长木楔,上面挂着一个绿色军用水壶,菜窖里面墙壁上又掏出一孔小的拱形圆洞,堆着土豆,白菜。
凉快吧?陆佰躺在了床上,问我。
我说,比外面凉快。
陆佰就得意地将一条腿搭到另一条腿上,脚掌开始颤抖起来,犹如小鸡啄米,冒冒然然地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陆佰为什么喜欢睡在菜窖里,没有人能说的清楚,有人说他是蛇投胎转世,也有人说他是蝎子变的,又有人说他被从城里下放,脑子受了刺激,还有人说他在地窖里搞见不得人的勾搭。有一次我忍不住问他,为什么不去上面房子里住呢?
陆佰大爷顿了一下,说,好好学习,以后你就懂了。
我趴在长条桌上写作业,直等到母亲喊我回家吃饭。有时我也待上一整天,陆佰大爷出去干活,我就待在菜窖里,这真是一个避暑的好地方。
陆佰在我们镇上的一个砖窑干活,负责出窑的活计。出窑很辛苦的,窑门拆了,推小车进去,光着膀子,窑内烟尘斗乱,闷热的温度瞬间可以让人汗流浃背,进出几次,头发眉毛挂满煤灰,人就变成个灰人人。晌午下工,烈日当头,他不回家,喝过半斤白酒,有些摇摇晃晃。食堂前面有一棵老槐树,一地浓荫,他便睡在北面的树荫里,直睡到树荫移开,强光刺目,站起来,揉揉眼睛,继续推着小车出窑。
傍晚,听见菜窖洞口的盖板响动,陆佰回来了,他跳进来,又是满身酒气。我收拾书包该回家了,他就躺到床上,说,出去了把盖板盖好。等我爬出洞口,盖好盖板,就听见里面已经呼噜震天。
我知道陆佰和我家好。父亲在外打工,春秋忙时,陆佰经常来我家帮忙干活。他爱吃莜面,母亲就做莜面。陆佰也不见外,自己端了脸盆,倒水,洗脸,洗手,沟沟壑壑般的手指裂纹里依然刺满黑污渍。盘腿坐在炕上,捏起筷子,挑一块莜面放到碗里,再浇上一股醋,啃啃地吃起来。母亲说些感激的话,陆佰不以为然地说,远亲不如近邻。
逢年过节,母亲炸了油煮糕,就让我趁热端一碗给陆佰送去,抑或压了粉条,也送些尝尝。夏天,父亲不在家,庄稼地里轮流浇水,有时排到我家时,该到半夜了,母亲就喊上陆佰,这样堵水,看水,通渠,导水有个帮手,在漆黑的庄稼地里干活也就不怕了。只要母亲招呼一声,陆佰肯定是去的,除非他玩骨牌玩得忘了。有一次,母亲好久都不见陆佰来,月光下,黑漆漆的玉米秆被风吹得唰唰地魅响,母亲独自在地里干活感到很害怕,等回到家时,天已经蒙蒙亮了,我那时还在炕上没睡醒。后来,陆佰来我家吃油炸糕时,满脸愧意地说,玩得忘了,好像是做了一件丢脸的事。陆佰就像我们家的一个亲戚一样,帮我家干活,也来我家吃饭,但有时也让我感到迷惑和难过。
那次放学,村里戏台上围着很多人看“打枪”(一种对弈游戏),我也走了过去。
陆树娃,你娘又去陆佰菜窖了?那个玩“打枪”的人挑起左眼皮,又这样问我了。
我就把眼睛瞪圆,骂他,你才姓陆了。
那人又挑起右眼皮,不信问你爹去。其他的人就跟着哈哈大笑起来。
我姓杨,我叫杨树娃,我感到委屈,感到不解。后来我再也不去戏台上了,远远地看见人堆,就向他们吐口吐沫。谁要再喊我陆树娃,我就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让石头向他们飞过去。
那天,我还是没有控制住自己,撑着胆子问母亲,有没有去过陆佰大爷的菜窖?母亲的脸竟然一下子绯红,停下手里的针线活,好像很生气地反问说,我去人家的菜窖做什么?我不敢再问母亲了,悄悄走开,扭回头,看见母亲右手捏着针在头皮上划一划,嘴在左手食指上吸一吸,应该是针扎手了,以前我就看见过。
陆佰好喝酒,挣来的钱除了喝酒,剩下的就都到骨牌桌上了,大概钱在牌桌上转几圈,最后也变成酒灌进肚子了。
骨牌桌上,人们都直接喊他陆佰,不管是年龄比他大的,还是年龄比他小的。我就看见过一次在牌桌上,一个小伙子指着他的鼻子骂他,陆佰,我操你妈。陆佰的鼻尖上沁出密密的小汗珠,回骂道,我操你媳妇。人们都前仰后合地呲嘴乐。陆佰说小伙子少给他五毛钱,小伙子却说自己上把牌已经结清了,陆佰就拍了桌子,小伙子便站起来做出要打架的姿势。围观的人赶紧把两人拉开,牌局就这样不欢而散。
陆佰其实有过一个媳妇。那是一个落叶纷飞的秋天,陆佰家突然来了一个女人,大眼睛,短卷头发,高个子,略微有些胖,坐在炕上,人们隔着窗玻璃向里瞅,陆佰就笑着走出来给大伙分发香烟和糖块,人们拿他开玩笑,他只呵呵地乐。
消息很快传开了,女人是陆佰从镇上买回来的,女人的丈夫在外面打工,从架子上摔下来,没了命,赔偿的钱被婆婆和小叔子霸在了手里,她就扔下两个小子跑了出来。女人很少露面,整天待在家里。陆佰每天在砖窑干活,女人就在家里洗衣服做饭,有走村窜巷的卖货车来村里时,才看见她提着篮子出去,买了东西便回去。女人穿得干干净净的,趿拉着一双红拖鞋,白灰色的短裙子紧紧地勒着屁股,裙子的边都是毛茸茸的,身上有股胭脂味,见了村里人也不怎么说话,口音侉侉的。每当吃晚饭的时候,美好的油烟香就从陆佰家飘了出来。村里人渐渐对她有一种神秘的感觉,男人们开始对陆佰羡慕起来,说陆佰打了多半辈子光棍,现如今走了狗屎运了,天天睡觉搂着个骚媳妇。
陆佰家有了媳妇,我不再去陆佰家的菜窖了,在街上看见他,我心里不知为什么感觉别别扭扭。陆佰好像和我家也有了隔膜,父亲在外面打工,陆佰也不来我家帮忙干活了。有一次,母亲做了炸糕,我看见她拣了一碗炸糕,我问,给陆佰大爷送去吗?她呆呆的,好像没有听到我说话,突然缓过神来,端起碗又把炸糕倒回到大瓷盆里,喃喃地说,凭啥给他。
陆佰的女人在村里神神秘秘的,不和人们交往。陆佰慢慢也变了,每天砖窑与家之间两点一线,人们在骨牌桌上也看不见他的身影,只是阴雨天砖窑雨休,陆佰就在牌桌旁边站着看看,也不上桌,衣服穿得格挣挣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他也不在菜窖睡觉了,搬了上来,窗玻璃擦得亮亮的。人们都说,男人还得有个女人管,陆佰有了女人的管束,一切似乎都充满了希望。
可希望总归美好,现实难免落空,陆佰又岂能例外。几年后一个炎热的晌午,陆佰在砖窑干活,一脚踩进泥坑,回家来换鞋,推开屋门,屋里没有收拾,陆佰有些奇怪,女人可能出去了,换了鞋又去砖窑干活,等晚上回来,还不见女人,搬个凳子在屋檐下坐着,久不见女人回来,心里发了毛,闷闷地抽着烟在院子里呆了一夜,女人终没有出现。
女人走后半年,最先发现陆佰出事的是砖窑的老板,好几天不见他来出窑,就找到村里。村主任领着老板来到陆佰家,屋里没见有人,就掀开盖板,跳进菜窖,发现陆佰已经死在了床上。
有人开始说陆佰傻,钱被人家女人把在手里,如今自己落得个人财两空。也有人对陆佰表示理解,钱不让女人把着,人家也不让他搂着睡觉。但是人们始终想不明白,陆佰打了那么多年光棍,为什么突然就想不开了呢?现在也没有办法考证了,陆佰已经死了,把这个秘密也带走了。
作者简介崔亚伟
汉族,河北人,业余文学爱好者,梦想是能在纯文学纸刊上发表作品,至今还在路上……
《同步悦读》是一个面向全球发布的新时代微媒体。每日更新,主推原创,分享精品;不唯纯文学,只重悦读性;读好文字,听好声音,欣赏有魅力的音乐。年6月2日被搜狐网站正式列入合作伙伴,发表在同步的作品,除微刊阅读外,同时拥有众多的网站读者。?原创作品
转载请注明:http://www.dongyamedia.com/yzjg/1388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