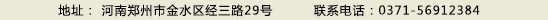小说丨故乡的原风景
我们在小的时候,熟悉的风景也只有自家背后茫茫无际的田野,通往胭脂小学路上那两排四季长青的树木,树木背后随着天气或光线变化或暗或明的星罗棋布的河流与头顶上飞过的鸟群......这些组成了无数双眼睛里的年年岁岁甚至一辈子,在一辈子没能走出胭脂村人眼里也许日渐单调,然而如果你是一个孩子,你去看,早中晚每个时辰天空的颜色与光线都不相同,田野里的路看上去条条框框细细长长处处相似,仿佛走一条就知道几百上千条全是什么感觉......如果你光看一眼就失去兴趣,那你一定是个外乡成年人,只有胭脂村的孩子最清楚每条道边上的泥鳅坑数量和花朵种类都不一样,最灵活的孩子知道明目的野菊花在哪片长得最多,还有红饭花,金不换,蛤馍草,粪箕笃,断肠草,蓝花草,鬼针草,鹅不食,牛尾荡,千斤拔,仙鹤草......你叫不出名字的花花草草多着呢,处处看上去风景一致的地方,处处皆有不同风景。
我猜,所有孩子都跟我一样,对树木背后充满危险的河流无限憧憬,越是大人明令禁止的地方,越是充满了新鲜刺激。只是有人胆儿大有人胆儿小,胆儿小的孩子必须听从大人话,对于自己所走的道路没有多余选择,
这真是个复杂的问题。谁也不知道胆儿小与胆儿大,没选择和选择更多,哪样能带来更多美好。
比如我,我没有选择地拥有一个正常完整的小家庭,自幼成绩名列前茅,我的路就是好好上学走到更远的外面去看一看。尽管爷爷奶奶和父亲都认为女孩子读书没什么用,但我的妈妈,一个经常板着面孔,像是全家上上下下欠了她什么,对子女说话非挖苦即讽刺的五官精致面色黧黑的中年劳动妇女,在上学这件事上,力排众议支持我。她说,能上学为什么不支持她上?难道胭脂村的女孩子就没有别的出路给咱们村长长脸?其实我清楚,不止她,几乎胭脂村所有留下来的有几分姿色的女人都对外面的世界充满憧憬。
如果这是属于我的人生路,这条路算是以后给我带来更多选择空间,也带来了一些别的不幸,要知道,一个女孩子不读书是容易不幸的,但是读到某种回不去了的程度会生出另一种不幸。正如我当年同情那些一起长大的小伙伴,对大人话言听计从,从不出去玩水,从不独去任何一个陌生的地方,天黑以前一定回家,还没成年就许给邻村的青年,默默按期出嫁,生子,逆来顺受并且老去,天天过一模一样的日子。别人满面生气说起这个世界的新鲜与快乐,她眼里只有谨慎与木然。这个世界的大跟胆小者是没有关系的。
吴昊属于特例,所有特例都必须胆儿大。他是个胆大的孩子。吴昊是吴双的弟弟。我还记得付一笑带我去吴双家玩时,我对吴昊的那种佩服。那时候我们上初一了,付一笑是暑假回来的,而吴昊才读小学五年级,可是他什么都知道。我们生在胭脂村,司空见惯的事物,其实除了老人并没有几个人注意到。比如野花什么时候开果子什么时候变甜龙虾最喜欢的诱饵是什么瓜要怎么判断是甜的,做饭放多少水才好吃,什么木头烧火最易燃,什么不好用,留下来做炭有哪些好处,往炭火里塞烤红薯,塞多少时间烤出来的红薯又香又甜......这些吴昊说起来头头是道。
吴昊非常聪明,动手能力极强,除了成绩不好。吴双跟吴昊两个人成绩都不好,他们父母有时候谁在家拿鸡毛掸子抽也没用,两个人的作业本上总是大片空白。小时候的我们习惯崇拜学习成绩好的,而我想起付一笑吴昊那些人仍然是一如既往的佩服心情,总觉得他们活得不同寻常。
他们富有同情心,看见乞丐要饭甘心情愿把手里没动的食物——比如一个刚刚烤好的大红薯让给他,骑着自行车愿意载陌生的路人,这和胭脂村人都不大一样。胭脂村虽然是一个并不富裕的村,却有强烈的排外意识,村里只要有陌生面孔出没,家家户户会互相提醒一定要把门窗关紧,乞丐来要饭,村民还要打听是哪儿来的,家附近的?东拐西转关系一靠拢,哎呀,沾亲带故,还认识,就多给点,话也客气了,有时还要寒暄两句,来的地方远了,就赶牲畜一样把人随随便便打发走。胭脂村民对外来者刻薄,小孩子们学样,他们警惕着每一张陌生面孔。
杨疯子见人路过就面目狰狞地告诫,陌生面孔专门来拐漂亮女人和小孩。
只有付一笑的大嗲和吴昊没有这些想法。我想起这两个极为善良的人,都是板寸头,痩骨嶙峋,穿着蓝色的破旧衣裳,背稍微有点点坨,活在这个世界上犹如影子一般,心里就有些说不出的难过,他们是我见过的唯一对可怜人特别好的人。对不可怜的人,比如家里人口众多喜欢七嘴八舌添是非的人,他们是没有交道的。别人也不跟他们打交道,平日里,他们就是别人眼里的可怜人,那些人看不起可怜人。付一笑说他大嗲会招呼远方的陌生流浪老汉睡在他家里几晚,有时候两个孤独的老头坐在大太阳底下卷烟丝,人家走的时候,虽只相处了那么几天,大部分时候还没怎么说过话,大嗲会送很多烟卷还擦眼泪,说:“老兄,前头保重勒。”
完全没说过话也不对,付强以前说,有个半夜他尿急,刚站在大嗲的黑屋子旁对着烟叶子站定了,听见背后有人说话,是他大嗲房间里传来的,那可是夜里两点啊,黑屋子也不显黑了,明晃晃的月光水也一样倾泻在床上,两个老头吧唧着手工烟,一人躺一头,大嗲问:“打哪儿来的啊?”对方说了个什么地方。大嗲说:“也有子女呢?”对方说:“有勒,七个,前头三个子后天三个女,都成家了,最后一个满儿子几个月大烧坏了,神志有点不清楚,前年弄坏了一把铁锹被他哥哥欺负了一顿,又是打又是骂,他是个傻子勒,不晓得那次就灵通了,来了气就那样出去了,一直没找着。老伴儿一急,去年病死了。我这还是不甘心,还是要找,不然前头老伴儿也不瞑目。”“也是可怜人。”“这天啊,要怎么过,就只能怎么过,一点办法也没有的。”“会好的,会好的,船到桥头自然直,都一样的。”“只怕船到阎王那头直唷......”
吴昊也这样善良,我在付一笑家并没有见过吴昊,不晓得吴昊与大嗲见面的时候是不是特别投缘,总之现在想来,那两个人当时尽管一个70岁一个才10岁,竟像来自同一个世界,有着同样的豁达,忍耐,能干与善良,甚至,还有一些苦楚。这苦楚,老的人手上脸上的如陈年树皮的皱纹都容易辨别,而小的,我也是从吴昊身上那件穿烂洗得发白的蓝衣裳和微微有点驼背的身子里看出来的,他眼里的光芒快活而软弱,似乎有点不自信,他不像别的男孩子那么莽撞。他其实是有力量的,小小年龄手掌大,手上皮肤粗糙,干起活来特别有力气,可他的力量不同于别的孩子那种生命的力量。他也跟别的孩子们交道的,甚至是入群的,也一起玩耍说话,很友好的样子,可现在回想起来,不知为何,总觉得他一直都是一个人,一个若有若无的小小蓝色身影,一个人去河边摸小鱼虾去田埂边抓泥鳅。一个人那样灵活地穿梭,在大太阳底下犹如一只温软的小兽为自己觅食与觅玩具,看见人就咧开大嘴笑,两只眼睛又大又空又光明,牙齿也大而稀少。
如今,大嗲与吴昊的名字早就在朱家镇烟消云散,胭脂村民格外避讳亡者,人们认为,一个人若是死了,就不要再提了,阴阳是两个世界,在阳间的人提阴间人的名字,阴间人要是听到了,与阳间接应上,阴气缠身要带来麻烦的。外头又有一种说法,上了60岁的老人是可以提的,花甲之年,那叫抓着了甲子。胭脂村长大的小孩子有时候等同于一只猫,猫死了不能埋,得挂在树上,挂得远远的,小孩子早天了,也不能用棺材装,只能随便钉个木箱子,埋得远远的。老人说猫有九条命,小儿魂和猫魂一样,容易牵鬼招神。再说,老人多少还有些回忆的价值,小孩的存在,对于胭脂村人来说,就等同于无了。
可对于胭脂村村民来说,大嗲的存在,是没什么回忆价值的。人们很快忘了他,并想不起来此处曾经存在过这么一个人。正如吴昊,吴昊淹死后才两年,他家附近的邻居就说:“是有过那样一个男孩子吧?是吧?我也记不大清了,是吴家的男孩子吧?”
胭脂村人并不多,邻里之间低头不见抬头见,倒不至于陌生成这样。然而吴家是有特殊情况的,吴家的大人跟周围人都没有往来。他们都不像是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付一笑与付一笑身边所有人。
付一笑身边的所有人,我知道的其实也就那么几个。付一梦,付强,大嗲,吴双,吴昊,还有付一笑的舅妈。
老人都说我记性好。也不对的,别的事情我都不记得了,然而别人不记得的事情和人,我却桩桩都有难忘的细节。
我还记得第一次去吴双家的情景以及刚刚进入青春期的付一笑的样子,她突然高了,露出光洁的额头来,说话又快又活泼,她的牙齿白而整齐,整个人洋溢着少女的纯净气息。那大概是她一生最美的时候。我们都13岁,刚刚念完初一的付一笑从红市回来,飞快地踩着自行车来找我出去玩。
“去哪儿呢?”
“啰嗦什么,跟我走就是了!”她头一摆,马尾辫在腰部摩来甩去。我第一次看到“明眸善睐”那个词语时,立刻想起的就是付一笑。
大暑假的,我骑着自行车就跟她出发了,心情新奇而轻松愉快,之前我每天都走同样的路,过着同样的生活......付一笑回来那次是我人生第一次自由去不同的地方,太阳在头顶暴晒,知了聒噪个不停,干活的人都去休息了,那可是暑天烈日的正午啊!而绿色是耀眼的,大片大片的绿,原野的绿,树木的绿,草地的绿,绿色的叶子张狂地伸出它们的经脉,叶面反射着强烈耀眼的白光,眼睛都睁不开了,唯独树影在地上摇曳,树影好像带绿色,快活穿梭着的付一笑也似乎是绿的,她的绿属于那个夏天又有自己的特色。她不同于那些树木原野的绿,更像一枚清晨的绿果,刚刚长成,沾着透明的露水,满身清鲜气儿。
因为河道星罗棋布,水涝灾害容易发生,胭脂村到处都种满了树,这些树都已经长大了,我们就在树影里互相追逐,看两边的风景刷刷刷在背后倒退,路是新修的公路,平坦宽阔,几乎没几辆摩托车自行车,更看不见一个人影,谁大热天地跑出来啊,只有我们,我们放肆地骑着,畅通无阻,其实也没有什么目的地,付一笑说好久没有回来了,得好好看一看,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落下来,我们都不畏惧那沥青一样黏糊在胳膊上脸颊上灼痛的温度,脸都红通通的,也黑了不少,但是开心啊,付一笑用力踩着脚踏说:
“什么是班车你知道吗?就是那种长长的公交车,比朱家镇的长途汽车还要大一点点,很干净的,大家投硬帀上去。”
那是我见过最自信快活的付一笑。这不同于我此前看过的胭脂小学的付一笑,也不同于几年后在朱家镇遇见的付一笑。我们这次碰面首先是在赶集的时候,她从人群里发现我,拍了下我的肩膀,我一回头就看见她俏皮活泼地朝我吐舌头,像是换了个人了,格外大方,但依然是那个人。是啊,我们都长大了。在互相别离的日子,我们进入豆蔻年华,这是一件很美的事情,两个从小做梦的女孩子从童年进入到了少年。也许还不算真正的少年,十三岁是一张少年之门,这就更美了,后头有那么多年头给我们憧憬,更美的是这过程里,我们保持了通信,不停地写。我们一边骑车一边不断地提起信里说过的人与事,时而哈哈大笑,时而放慢脚步长吁短叹。
付一笑面露惆怅之色地说:“我们语文老师说,青春期忧愁是最多的。长大以后还会有很多很多的烦恼。那什么,嗯,就是你,你最期望长到多少岁呢?”
我想了想:“十八岁吧,又已经成年了,还是不如十七岁好,可是十七岁离十八岁挨得太近了,会让人感到慌张的。我渴望长大,却,却不喜欢变成完全的成年人,那还是十六岁最好。你呢?”
付一笑爽快地回答:“我觉得现在,现在就挺好的。每一个当下我们都应该珍惜。”
那确实是她最好的当下,在我所憧憬的繁华红市上学,成绩优秀,活泼开朗,老师和同学都喜欢她。唯一难过的事情是她大嗲去世的时候,她没回来。
付一笑怅然解释:“我爸说,人走都走了,人老了都要走的,七十多岁已经算高寿的。活着的人日子要继续,我们全家人一起走,路费也多。我妈妈为这个跟他吵架,我最怕他们吵,就说不回去了,不想回去。人都去世了还回去做什么,大嗲活着的时候那些回忆被记住就好了。我只要他们不吵,怎么样都好。”
胭脂村人就算不喝酒不做梦也讲究醉生梦死的态度一一活着就只管活着的人和事。
我不甘心:“大嗲对你们那么好!”
她的回答不合常理人情,又让人心服口服:“对啊。这样大嗲留给我的最后一面,永远是我心目中的大嗲。”
我们见路就行,朗朗大晴天白日,只逢了几个扛着锄头戴草帽佝偻着背准备去地里干活的穷苦老汉,这又让我联想到大嗲,我们共同驰过一片树影进入到没有遮蔽的阳光下,付一笑低沉的情绪渐渐被阳光点亮。她兴奋地说着笑着,讲在新学校的见闻,她说:
“我跟你讲啊,有一次,下了很大的雨,我们老师让我们自习,就跟你提过那个特别凶特别凶的老师,老是板着一个脸,平时大家都特怕她。那天特别特别安静,然后有一个家长来送伞,我跟你说有多搞笑,哈哈哈哈哈哈,我都要笑得说不出来了......你知道吗,那个家长很胖的,他穿着个黑色雨靴,往门口叉着腿站着,门口一下子就黑了,因为那个人太高大啦,他平时也很严肃的,他那天刚刚往那个门口一站,就‘噗一-’放了一个好长的屁。我们那天安静得真的是只有翻书的声音,听到之后笑疯了,连我们老师都忍不住笑了。”
“你知道吗,我们班上有个同学,他家有电话,他家的电话号码说一遍我们全校人都记得住,你猜是为什么......因为他家电话号码是,就是说’气死您吧气死您’哈哈哈哈......”
“我们英语老师好漂亮的......我们英语老师名字都很有趣,我们都叫她miss兔,miss兔的妈妈有时候还会到我们学校来,我们都叫她兔妈妈。兔妈妈有时候会跟我们全班发大白兔奶糖吃,她说miss兔只吃肉不吃蔬菜,这样不好,对身体不健康,我们要一起批评和劝劝miss兔......什么?不胖啊,不不不,我们miss兔一点都不胖呢。就是,就是有这样的人嘛,这个世界上就是有人只吃肉不吃蔬菜,她爸爸妈妈都是教授,她有钱只吃肉.......她很年轻,很漂亮,很苗条,她的头发像水一样光滑,皮肤白得像雪一样,一笑起来前面两颗牙齿尖尖的,就是,就是很像只兔子。”
“我们有个同学家里好有钱的,他爸爸好像是黑社会的,他每天都有保镖送他上学,吃饭也不去食堂,还有保姆给他送了来,你知道什么是保姆吗?保姆就是专门给到别人家里做家务活,然后别人给钱的那种。给钱很多呢,有的一个月赚的钱比当老师一年的钱还多.......我妈妈也给一个有钱人做过保姆,但是我爸爸不让她去了.......”
我们走在一起,人们都用令我羡慕的欣赏目光看她,她灵动漂亮,穿领子上绣有小花朵的白色衬衣蓝色格子背带半身裙,浑身上下干净利落,衣领是衣领,白袜子是白袜子,马尾辫自然洒脱,扎着一个纤巧的蝴蝶结,她再也不用戴过两天就枯萎的大红花了。她还是见了好看的花就采,用细草捆成一束束插在自行车扶手前。我惋惜地看着:“折了多可惜啊。”
她满不在乎:“这长得到处都是,不折都没人欣赏,我折了这花起码有我懂它。”
我们到了陌生村庄,汗水顺着鬓角往下流,去有人家的地方讨要井水洗把脸。南方的院子都是敞开的,家家户户用摇井,用手在上面压,水就出来了。付一笑见一个大妈正在院子里洗晒竹席,就过去说:“伯伯,我们在这洗个脸好不?”胭脂村的风俗都是这样的,比自己父母大比爷爷奶奶又年纪小的长辈,男女都叫伯伯,比父母年龄小的,男的叫叔叔,女的叫姨。
大妈乐呵呵地说:“好勒好勒,你们洗就是啊。”
付一笑伸出纤细嫩白的脚腕灵巧地一拐,自行车就停住了。她笑着跑过去,还招呼我,倒像是她才是这里生活已久的主人。
大妈长时间从头到尾地打量付一笑,赞赏道:“你们这两个姑娘是哪家的啊?这样秀气,又这样聪明相,看着读书就是前名的角色。”
我说:“我们骑自行车骑到这儿来了。她聪明,她在红市上学,每次都是班上前三名!”
大妈一脸钦佩的神色:“哎呀,红市里前三名的角色啊,我说这姑娘生得灵气相吧,这是到这来走亲戚了?”
付一笑答:“我家以前是胭脂村的。谢谢伯伯,我们洗好了。”
大妈殷勤地说:“胭脂村出漂亮闺女,一点也不假的......这就洗好啦,要香皂不?”
付一笑甜甜地说:“不啦不啦,伯伯我们走啦。谢谢伯伯。”
大妈还挽留我们坐会儿歇气。付一笑推着自行车礼貌地对大妈说:
“伯伯我们还有事情呢,我们下回来玩。”
这就是胭脂村的客气话。胭脂村人见了都说:“吃了吗?”遇到饭时候见熟悉的路人经过要说:“进来吃不?”客人急着走了,就说:“要你在这儿过夜呢,多留几天。”即使没有菜,也说:“菜都是现成的,您急着走什么呢?”
同样的13岁,我赶不上付一笑,傻乎乎地问:“我们还有什么事情?”
我想象以后还有很多个这样的暑假,这样的闲暇时光,我们骑着自行车在一条条新修的公路上飞快驰行,边说边笑。我以为以后大概就是这样了,如13岁这年夏天,甚至更自由欢畅。那是我第一次擅做主张出门,长大成人的感觉这样好,去跟陌生人打交道的感觉这样好,我甚至有点后悔选择16岁为心里最渴望的永恒时光,巴不得赶快满18岁,赶快成年,那样,所有未知的精彩都会敞开了。
那个下午,我们等于什么事也没做,只是一直在骑自行车,我却感觉满满的很充盈实在,像是说了很多话,听了很多故事,去了很多地方,并且是一些从未做过的事,从未去过的地方,也从没人跟我说过的话。
人生最欢畅的事情不就是这样吗?以后我们会长得更大,会去更多不同地方结交更多好朋友说更多想说的话。
其实,谁知道呢?这儿村村相连,家家户户房子雷同,一样昀沿河而居,一样的小屋敞院,一样的流水潺潺,又一样的摇井和晒绳。
嗨,胭脂村,一点特色也没有。胭脂村周围,也和胭脂村一模一样没什么特色。有特色的是两个13岁的少女在无人的乡间大道上飞快骑单车,痛快享受青春初期的诗意与灵动。
我们热得满脸通红全是汗水,洗了脸后清爽很多,然而实在累不动了,就推着走。大太阳下绿的绿得耀眼,红的红得灼艳,水白花花地闪耀光亮,房屋前飘晒的衣服都干了,红砖黄泥在草里面,窗内都是闲适的,扑扇子的扑扇子,敞着两只光脚丫对着大门午觉没醒的睡午觉,还几只吐着长舌头的丧家之犬——痩骨嶙峋,在垃圾堆里觅食。
一点多余的风景也没有,树也是寻常的树,然而却是这辈子见过的最动人的风景了。
易丹十路
李小天
情感
时评
鉴书
观影
非虚构
走出象牙之塔
来到十字街头
众声喧哗的世界里我们有自己的声音赞赏
人赞赏
治愈白癜风多少钱北京治疗白癜风特色医院转载请注明:http://www.dongyamedia.com/yzjg/629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