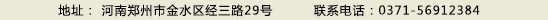红粉系列二nbsp完美落幕
堕落原来可以这般的酣畅快意!
风鼓着我,大地扑面迎来。身后或许还残留了些许尖叫声,我亦不顾,只管扎进大地的怀里,染一抹红尘,只为在黄土上绽放出硕大的红花来。
那一刻,我奇怪地听到掌声响起来。天边的血色残阳正在引退,暮色四合,天地的大幕缓缓而落。捱了这么些年,到底捱到落幕了——
戏终于演完了。风已起,花亦落,日暮东风怨啼鸟,落花犹似坠楼人。
我萎在一片血肉斑斓的狼藉里,仰望那个还留在舞台上的男人,掩了面在啜泣。我既得解脱,转而好生怜他。戏份还没完的人,还要尽心尽意地演,不能做自己。
有人在唤他,阴阳怪气的:石君侯,石君侯。唤了两声,到底失了耐性,阴厉地喝:石崇!没完了你!还不快上车!
金谷别馆的绿珠台下,囚车在静候。君侯哭完了,就该进去了;进去了,就该推往西市斩首示众了;斩了首,才轮到他的戏落幕。
早知道演戏这么无趣,我何必上这舞台来云袖翻飞一场?1
可是年长才知非,二十年前,我哪里明白这道理?
二十年前,我是山野小丫头。玉林县双凤乡的绿萝屯,窝在深山的怀里,山是大家伙儿的粮仓,想吃什么都到里面去取,野果、野兽,荤素齐全。山还有别的妙处,是除了娃娃没人知道的——山的腰间挂着一汪碧幽的水,水边有石。坐在石上探出头去,水里会浮出一个自己来。
山里的娃娃不多,水里那个绿珠,就是我的玩伴。我日日到水边去找她玩,花样翻新。我插了一头烂漫的山花,只为装扮她;我说话,她就听;我怕她闷,就给她唱歌,她怕我闷,会跳舞给我看。我们玩得不亦乐乎,我做着我自己,整日里都开心。
那天我们正在水上水下对着舞,突然听到一声响。是什么东西掉到水里,一圈一圈地漾开,很快就侵犯到了水里的绿珠,她转眼被揉皱、晃散,消失了。
对面杵着个太阿婆,看起来跟深山一般年纪了,脸上手上,俱是层层叠叠、沟壑深深。刚才把水下绿珠冒犯走了的,是她的一颗泪。一颗泪接着一颗泪,串成晶莹的哀伤。
我不怒转惊,迟迟疑疑问:“阿婆,你哭什么?”
阿婆笑起来,是不快乐的笑,她在嘲笑自己:“我也在你现在站的地方,跟你现在一样地跳过舞。”
原来是我占了她的地方。我忙轻跳开去:“那我把石头让给你。”
阿婆的笑又开阔了些:“傻娃子,我还跳什么跳。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了。”阿婆低了头,对着水说话,“今天你跳,还有我看,那时我跳,只有水看。水啊水,你还记得我吗?”
原来,跳舞是可以跳给别人看的。
我低头,先看到水里的绿珠,很饱满的。水的另一头,漂着一个苍茫茫、颤巍巍的干瘪太婆。太婆像我这般大的时候,一定就像这边水里的人儿,可现在她在水的那一边,苍茫茫地干瘪。太婆像我这般大时的情形,我不知道,水不记得,太婆自己还记得真切么?
水跟镜子一样,都是最没记性的,只记得当下一刻,转眼就不留痕迹了。等我到了水的那一边,成了太婆,这边的绿珠也不会被记住的。
我突然觉得冷,水里的绿珠抱紧了胳膊,我的心还是一阵阵的寒和颤。我哭起来:“太婆,水以后也不记得我的。”
阿婆耸了耸背篓,已经抬步走了。她不看我,只说:“没关系,到时候你来找我,我还记得你。记得你今天跳舞唱歌,好看又好听——就怕那时我已经不在了。”
回到家,我跟阿姆说。阿姆惊道:“那个太婆我知道的呀,我小时候,她是屯前屯后出了名的第一美女。跳舞唱歌,好看又好听。”
我忙问:“你见过吗?你还记得她跳舞唱歌?”我该去告诉太婆,水不记得她,还有阿姆记得。
阿姆笑骂道:“我咋会见过?别说我,就是我们屯,也没人见过的。她是前屯的人,隔了一座山呢。又没亲没故,又不是有什么事,难不成专为了看她翻山过去?”
我一夜睡不着,第二天一早就跑去水边,山石涧渊幽幽瘆人。水真的什么都记不住。昨天我一头的花,今天它就忘了,让我素寡着头,愁云惨淡。我的舞再好看,竟没人看。
我对着水散了发,用手慢慢的理。昨天的那种阴寒恐惧,渐次又咬啮上心头。我不想变成水那边的太婆,我尤其不想变成太婆后,谁都记不住今天的绿珠。我想有人看我舞,听我唱,我想有人记住我。到我老了,到我死了,还有人记得我,记得我今天的样子。2
突然的巴掌声惊断了我的痴想,我直跳起来。赤脚跑开好几步,才停下来。
水的对面,昨天阿婆站的地方,现在生出了一大队人。好大好大一队,很多人,很多车,都是金灿灿亮堂堂的花人的眼。
拍巴掌的是一个玉冠紫衣的男子,长得好俊,白生生的脸,可惜有点老。他笑吟吟道:“唱得真好。心有所感,哀怨凄婉,有向死之思,莫非是‘懊侬曲’?”他说话用的腔调和词语都怪怪的,我要琢磨好一会儿才能明白他的意思。敢情刚才我想心事的时候,心事就乘着小调从嘴里溜出来了。
我胡乱地点头。突然高兴起来,这是第一次,我唱歌有人听。以前我唱,只为自己开心。我的歌,山会听,水会听,鱼鸟花草、流云山风都会听,但今天是第一次有“人”听。听了还夸我,还用两个手掌直拍,我很满足,从来没有过的感觉,美妙到飘飘然。
原来,一个人做一件事,有别人听着看着,会特别的不一样。一个人活着,要落在别人眼里心里,才特别的有趣味、有劲头。
我不管那人是谁,说:“我还会跳舞呢。你要不要看?”
那人的眉毛很好看地跳了跳,他的声音也欢跳:“好啊,不胜荣幸!”
我的脚在石上轻点两下,就旋起来。我能下腰把身子拧成一个圆,能旋转到好像飞起来。我从来没有跳得这么兴奋过,披散的头发飞啊飞,飞迷了我的眼。
有一瞬间我的眼睛逮到了什么,错愕到下一瞬间,身子才停下来,僵立着看水对面,心里直发凉——
那个人不在了。金灿灿亮堂堂的车马都还在,可那人不见了,跟在他后面的人也都不见了。没人看我了。我的心飞在半空踩不到实地,晃悠了一下,重重跌落下去。
没人看我了!
……柔柔暖暖的气息痒痒我的耳垂和脖颈,我猛一转身,惊得叫起来。叫声引爆了他和身后的人一大片笑声、掌声和喝彩声。他的手里捧着一把山花,似笑非笑地靠近我,花粉在我鼻尖蹭出一抹鹅黄。他软语温存,喃喃如梦呓:“送给你,为你的——嗯,‘昭君舞’,果然体如游龙、袖如素蜺……”
我的脸燃烧起来,我的心再度开始飞翔。他用鲜花和掌声,还有他的注视、他的欣赏,将一块寻常的青石变成了舞台,也将我从一个为自己活着、让自己开心的山里娃,变成了舞台的女主角。
“石大人,该启程了。”旁边有人低声催促。三声之后,他终于从我身边退了退,退出巨石,退到水的另一边。他翻身上了马,缓缓前行,频频回顾。隔着大队人马,他的眼神里有无限的未来,无限的不确定。在消失前的一刻,他抬手向我招招。手招完后,指头一根根缓缓收拢,掌化成了拳,好像我就在他拳中。3
当天晚上里长就来了我家,告诉阿姆阿爹,不要把我许人,说有人要了我。那人是谁,里长说不清楚,什么时候来接我,也说不清楚。只知道是从京城洛阳来的,洛阳可是老远老远的,到交趾去办公事,交趾也是老远老远的。
阿姆阿爹听了,且惊且喜且忧且惧。事出突然,自然惊。女娃总归要嫁人的,嫁个金龟婿,强过跟着穷汉吃苦,是喜事。只是女儿远嫁了,别说受委屈时娘家帮不了忙,只怕以后连见面都再不能,岂不可忧?但女婿来头太大,大得连里长都不知道,又是决计得罪不起、大可畏惧的。
一家人守着里长留下的十大斛珍珠,一夜难眠。只有我是欢喜的,我喜欢他喜欢我的样子,喜欢他给我的舞台,喜欢他给我的天地世界。那个世界里,会有人看我,有人喜欢我。被别人看,被别人喜欢,这是让我高兴的。
我愿意把自己交给他,交给他属于的那个世界,我向往那个世界,虽然我对它一无所知,但它在山外头,很远又很大,这一点就足够。半年后,我被带走了。被带走的不止我一个,还有一个叫红蕊的,竟是太阿婆的外孙女。我们很快成了朋友,一桌吃,一床睡,可喜一路上不至于寂寞害怕。
我心里更喜的,是变化了的未来。我再不会变成水那边的太婆了。太婆只有山深处一块孤石、一汪静水,我却有了观众,有了我的舞台,舞台的大幕正在拉开……4
两个月的颠簸后,大幕终于彻底拉开了。大幕后面,是注定要成为我人生舞台的金谷别馆。
好绚烂的舞台!园里的一切都让我晕眩和自卑。厨房里白蜡作柴,异香喷鼻,涂抹墙面的香椒泥烈香袭人。伺候我的丫头,个个像我的主子。她们衣服光鲜,妆艳态媚,说好听的官话,伶牙俐齿,知道屋里每一样东西的名称和用途,漱口和喝水用不同的杯子,洗脸和擦手用不同的帕子,早上和下午插不同的头花,去前殿和后院穿不同的衣服……我只有眼花缭乱、手足无措的份。却不愿像红蕊那样,不假思索地俯首称臣,把谀富谄贵的艳羡和折服明白挂在嘴边、写在脸上。红蕊每有新发现惊叹于我时,我唯有借了路途的倦,病殃殃地万事假装没兴趣。富贵太强大,我在其中,要小心不伤了自己的尊严。
我怕。这是一个太大的世界,太大的舞台,我在上面太渺小。无端端被淹没在一百来个女娃娃当中,她们都年轻、都漂亮、都善歌舞,我置身其中,就像一粒沙置身沙堆。如果我比较老而丑,可能反而出众些,就像金笛老娘。
金笛老娘是大教坊的大当家,负责所有人的衣食住行、荣辱升迁。我们一日日地挨金笛老娘的训斥,也学她的笛子,学歌舞弹奏,学识字断句,学举止谈吐。
度日如年。幸喜在如年的日子中认了些好姐妹,莞儿、樱儿、瑶儿,不过早我半年一年来,个个出落得珠圆玉润,熟透了一般。我和红蕊随了她们,学会了婉转莺啼、软语娇嗔,学会了穿丝绸的裙、插锦缎的花、擦桃花的胭脂、染玫瑰的唇。5
终于在一个红烛高照、灯红酒绿的豪夜,我们被带向那一片奢靡的流光溢彩——我的舞台。我和红蕊在暗夜的甬道上手绞着手,任凭掌心返潮,任凭隐隐的兴奋滋生蔓延,燃烧双腮。我们的第一场演出!
但,一切在进入金碧大堂的一瞬间破碎。但见酒溢肉香间,一大帮二八少年,束袖马靴、髻散鬓乱地正喝得痛快。没有期待的目光和掌声,我们的出现如同空虚。
我们按例坐了、立了,横笛、竖萧、抱琵琶。丝竹渐起。红蕊缓步立在席间,展白紵,作飞燕起步式,回头示意我。
我微点头,暗暗运气,沉丹田,聚腹胸,贯透鼻额,轻轻破唇,缓缓吐词——
华山畿,君既为侬死,独活为谁……
啊——呸!!
粗暴的一口痰,生生截断了我。一个半醉的小子跳起来,扬手赶红蕊和我,嘴里嚷道:“臭娘们,你唱的什么玩意儿!”
我惊惶而答:“是……是懊侬曲……”
“懊侬曲?”少年坏笑道,“你唱得不对,懊侬曲该这么唱:哥哥你不来,妹妹我怎睡得着,半夜里解开衣,我……”
少年的假声怪调,引得众人开怀野笑。少年受了鼓励,越发的张狂放浪,转身又揪红蕊的襟,醉意迷蒙道:“还有你,跳舞穿这么严实干什么?紧紧的展不开手脚不是?”
一旁有人混叫:“孙秀!不是姑娘展不开手脚,是你不便展手脚吧!”
孙秀自嘲道:“都一样,都一样……”
众人越发调笑:“摸来摸去还是衣裙,没有肌肤之亲噢——哈哈哈——”
金笛老娘已经闻声进来,虎了脸呵叱我俩下去,另换两人上前献艺。
孙秀又叫:“哎——别走啊,干嘛走了?”
金笛老娘赔笑道:“小丫头不顺爷们的眼,自然要再换两个好的。”
孙秀沉沉点头,道:“对,要换。要她们别素着一张脸,太清淡了……没看头!”
我退到一边,恨极了地看客人们推杯换盏、赌酒斗气、猜拳投壶,也有横卧案下的,高声吆喝、酒臭熏天,更有烂醉狂儿,随意捞着侍女舞女的衣裙,便行轻薄之事。我们只是晚宴最华丽的装饰花边,被酒肉污了,还可做抹布。6
第二日依旧。我唱不过半支曲,又被众人轰下去。不同的是,一夜之间,红蕊却开始受欢迎,她才一亮相,碰头就是一片彩,她再一亮相,又是一片喝彩。越发衬出我的清寡和冷落。我百思不得其解,临到睡时,才恍然想到了因缘:舞还是白紵飞燕舞,红蕊的小衣外衫,却是半解!
第三日宴前,姐妹们在后院教坊上妆,红蕊在我身畔,我只怕昨晚错想了她,偷眼斜望去,她的衣襟果然松散。低低地盘一个倭坠髻,复以木梳挑出两缕发丝来,透出一丝鬓乱酥媚,深有意味一般。
我的心一跳,又一跳。以红蕊的伶俐,已经知道如何取悦于人。我又如何甘居人后?只是我不惯这样的妆,暧昧得让我失了自己,讨厌自己。我的石黛在妆砚里来来回回地碾,铅粉在掌心里反反复复地磨,把我的心都碾磨碎了,到底还是没用上。7
自那日后,夜夜笙歌皆如是,夜夜忍气吞声、气结泪流。日间还要被金笛老娘迫着学吹笛,指法颤、叠、滑、花,运气缓急粗细,半日下来,指僵唇燥,苦不堪言。
那日宴前备席,姑娘们聚了上妆,叽叽喳喳的。我的铜镜里,却只有个枯坐垂泪的人影儿。金笛老娘见了,冷笑冷言地刺道:“你要真想别人待见你呢,就自己有本事挣得上大门面大舞台去。只不过,大排场自然大规矩。错了一声音喉,就是一颗人头。要是没点能耐没点担当的,再不要在这里歪歪唧唧生牢骚了——小心白头生皱纹,越发没人看了!”
一言未了,旁的女人,俱是大笑。
我竟听不懂,亦懒怠弄懂。瑶儿、樱儿生了怜惜,隔着几个人给我送眼神,我亦懒怠接应她们的安慰。只管一味地装聋作哑。宴上情形依旧。红蕊又得头彩,我又遭叱被贬。我在暗处冷眼看热闹的红男绿女,从红蕊想到太阿婆,复想到自己花般容貌,水样年龄,竟这般日日老去,如何甘心做了此间粗陋儿郎的酒色背景!心一横,退出堂来,直奔后院妆台。脂粉、石黛俨然都在。我坐定了,喘口气,对镜画眉,眉飞入鬓,眼角荡霞,是一个挑逗的妖妆。
但,妆没能画完。随着一声响,双钩云藻纹镜被一支金笛拂落在地。老娘自来横眉立目的,却从不曾如此满面暴怒。
“这是为何?”我立了身质问。
“你问我为何?你化这样的妆做甚!”
“你管我做什么!”我不管不顾地犟嘴。
老娘恶骂道,“没出息的东西!你只巴巴地记得讨人的好,遂人的意,谁又讨你的好,遂你的意?你把自己当什么了?”
我气极而泣:“我能把自己当什么?我歌我舞,没人听没人看,一切为了谁?”
是呵,谁曾对我著一只眼?我歌我舞,竟是为谁?若说只是为自己开心,我留在山野就好,又何苦来此间受罪,遭人白眼?那个喜欢我歌舞、带我来此间的男子,他又在哪里?
“糊涂!你自己都不把自己当回事,更有谁待见你?”金笛老娘以指叩几,恨恨不已,“我说了,你若想人高看你,须自己挣上大排场去。会飞的鸟不能学爬,你若把自己毁在下席,以后就永无出头之日了!——滚下去!把晌午教你的曲子再吹三遍去。”8
下房的回廊牵着后园的胭脂池,我独自坐在池边石上,泄恨般一遍遍吹新学的笛曲“思归引”,登云阁,列姬姜,拊丝竹,叩宫商,宴华池,酌玉觞……此恨何及!
吹到第六遍时,席散后。红蕊照例还没应酬妥当,瑶儿、樱儿已经下了场,背了老娘偷偷来慰我。
月色已西斜,险险地挂在天一角,摇摇欲坠。我问:“什么是大门面大排场?”
小小的瑶儿推着樱儿,调笑道:“这事你最该问她!她才高升了,你竟不知?再不是我们这般下席女了,以后只怕都见不着了!”
樱儿且羞且喜,嗔道:“瑶儿!你再闹,我要恼了!我不过去了半月,你就不认姐妹了不成?”
原来金谷别馆的筵席,是有级别的。客人带来的车夫轿夫仆从手下,随意聚在大堂里,劣食烈酒、粗瓷糙碗,也能让他们尽兴痛快,是为下席。瑶儿在中席,招待的是寻常客人,只有雅士贵客,才与主人一道入上席,上席的丝竹之雅、歌舞之美、饮食之精、排场之奢华,在整个京城都是出了名的头一号。
酒也冽,乐也清。上席的客人都是风雅之人,品得出音韵,赏得懂文辞,“阿弥陀佛,可没有那些胡吃海喝、浪笑野叫的。倒也有淘气的,不过便是淘气,也样样儿精致。”樱儿笑道。便在今晚,主人还就着她的玉手满饮了一盅,要拉她温存。
这才明了老娘的话。原来只要如此这般。我不必委屈了自己去曲意悦人,坚持做自己,终究能找到真懂我的人,能挣得我的真舞台,真真赢得众人眼、众人心,还能见到我的主人,赢回他对我的喜欢。
我心神向往之,只道:“樱姐姐,这可不是要恭喜吗?”
“是啊是啊,”瑶儿爽然脆笑,迫道:“你应允了的吃请,可还没兑现呢。”
樱儿温婉啐道:“竟没见你这样馋嘴猫的,到底还是小孩子!——我兄弟过两日就押租来京城,自然带些家里的小食,桂花糕、玫瑰酥、槐花蜜馅儿的小松饼,到时候还怕堵不住你的口?绿珠,你也要来。”直惹得瑶儿跳了脚地拍手,欢笑串串。
我忙应了:“那是自然。我这些日子,也想着家里的阿姆,屯上的老婆婆……”
不觉就这般聊到了东方泛白。樱儿起身掸衣,笑道:“哎呀了不得了,再不睡,今儿夜里筵上酒一熏,该瞌睡了。我们还是散了吧。”我总记得樱姐姐说的桂花糕、玫瑰酥、槐花蜜馅儿的小松饼,可我到底一样也没尝到。我也总记得她说了最后一句话“我们还是散了吧”,我们竟真的散了。樱姐姐的哥哥来将她尸首领走的那天,我竟不得见。一般陋乡僻野的男子,那进得了金谷别馆?就在后角门外领了几吊钱,与家丁仆妇交接了完事。
我与瑶儿都悔了几个月。那日真是聊得太晚了,要不是睡不足,樱姐姐的纤纤指何至于在古琴弦间堪堪滑错一步?徵到变徵,不过一阶,主人竟这般精通,当下便听出来了。客人也听出来了,洋洋地斜了眼,要看主人的笑话。樱姐姐的命不过是一杯水,轻易地便冲走了客人嘴角肮脏的嘲笑。
主人的体面光洁如新。9
半年后,我和瑶儿都升到了上席,我终于挣到了我要的舞台,也见到了我曾经朝思暮想的那个男子,但樱姐姐尸骨的那份寒,一直留在我心头,物是人非事事休。
我在席上翻飞,我给宾主奉酒,我的笛声绕梁,几次三番,他都不认识我。我曾以为他喜欢我,樱姐姐一定也曾以为他喜欢她。如今才知道,他除了自己,谁也不喜欢。
但我仍然喜欢上席。上席的客人通音律、善艺技,而主人尤胜。我歌、我舞、我吹笛,其中意蕴,丝丝如缕,他们都品得出。他们含笑的眼神、微颔的头、叩节的指,都如泥如大地,滋养我的生命开出花来。
闲下来静思时,心也生悲凉。曾几何时,自己歌舞就能开心,如今离了别人的赏识,我竟无力让自己快乐。自己的快乐系于他人的眼,岂不可悲可怜?可是——
谁不怕寂寞,谁不怕在寂寞中空老?我在上席的酒色迷离中绽开自己时,我发誓我的花要绽放到艳绝古今时,到底庆幸自己不会变成家乡的阿婆。
就冲这一点,到底感谢这个当年带走我、如今不认识我的男人。10他重新认得我的那天,是瑶儿的死期。
我不知道杜将军是谁,但我至死都恨他。与他同来的王大人,显见的不胜酒力,尚且肯偎在莞儿的怀里勉力而饮,杜将军却有意停杯。这个高大的白面男子,嘴角叼了哂笑,要席间主人的好看。
“石大人今儿可是让满京城都见识了!国舅爷自己送上门来,白白讨了个没趣,真真落人笑话。”
主人半敞了怀,满面泛光地曼声道:“哪里哪里。我知道自家东西呢是多了点,房子大了点,吃得好了点,女人也美了点,王国舅看了不舒服,要跟我斗斗狠,比比阔绰,原也是常理。只不过他不该拿珊瑚来嘛,那玩意我家太多,平日里都恨不得当柴烧。我打碎了他一个,原要陪他两个,他又不要。大将军若不嫌弃,在下也奉送一个?”
杜将军的白面阴了一下,讪讪道:“不必了,我家既没有皇上赏的珊瑚供石大人敲,无功也就不敢收禄。”
我害怕看杜将军那张掩不住阴郁和寒碜的脸。在上席,我看到了太多这样的脸。那些脸原是大同小异的,进门之初,惊愕艳羡至于怯怯,每每变色。酒酣色迷间转生出纵欲沉醉的红光来。而那坨红退潮之际,恨恨不平的嫉色和无端的仇意,竟是掩都掩不住。
“我这么多年竟是白活了。”我肯定,离开石家金谷别馆时,好些人是这般懊恼和嫉恨的。
我还肯定,其间的微妙,主人也一定是知道了。他不仅知道,而且很享受别人这样无端的懊恼和酸溜溜的醋意。
人活着,多半原是活给别人看的。美貌要人看,年轻要人看,才华技艺要人看,荣华富贵、锦衣玉食都要人看。否则衣锦竟夜行,富贵不还乡,发达了不设宴旧友,福禄寿禧不落在他人眼里,点燃羡和妒的火,到哪里去觅那一份矜夸荣耀的意气风发?
迟至千余年后,高级茶座酒楼咖啡厅,还要设了透明的落地大玻璃,让华贵的人坐在橱窗里,少少半是方便他们边吮咖啡边望街景,大大半倒是为了把他们的华贵化作风景,不动声色地供路人眼热眼红。发达了的人,每每热心同学会,乐意会老友、返故地,道理都一样。
这道理,我懂,他更懂。他要他的华贵优渥灿烂如太阳,明晃晃地照出世人的黯淡和寒酸来。他活着,就是为了这一份绚烂。他明白白地矜夸和炫耀,惹来众多下贱的追捧,也无端端惹来众多黑暗的厌恶和仇怒。我分明看到杜将军体内生出这厌恶的毒来。将军毒发,瑶儿身亡。
他固执地不端杯,就是不给主人面子。主人半恼半怒地,要瑶儿务必劝饮。他只戏弄般乜斜着瑶儿,无动于衷。
我那时还不知道石家待客的规矩,所以也不明白瑶儿的泪为何滚滚地下。僵持不到片刻,主人的手一挥,瑶儿被带下去了。主人的手很快又挥了两次,又有两个侍女被带离了席。席间突然从暖春凝到了酷冬。莞儿立在我身边,扑簌簌地抖,主人白皙纤长的指头刚对着她,她便瘫软在地,大哭出声来:“求大人不要杀我,求……”
我突然就全明白了。杜将军不过要挑衅主人的风光,以浇灭自己的嫉火,而主人也不过要粉碎他的挑战,保全自己的体面。如此的拉扯不到一支香的功夫,竟是三条人命!而两个男人之间的那杯酒,还安然静卧在杜将军几案上,泛着葡萄美酒幽深的光泽。11
之后的事,都是莞儿告诉我的,我竟全然不知。
杜将军绝然想不到,一个女子竟会抽了他的剑。剑和酒并排置在他面前,女子当面跪了道:“奴婢为将军献一曲祝酒歌。要么,将军满饮此杯,要么,将军的剑饮我的血。奴婢无能,生前劝不进将军的酒,死后便是做了鬼,还是会跟在将军后面献曲劝酒的。”
这个女子,是我。
主人大获全胜。在雷动的爆笑和轰然的掌声中,在我哀婉情切的歌声中,杜将军端起琥珀杯一饮而尽,而我也不知何时被主人揽在了怀里。
他眼含笑、面含春,用唇喂我的酒,百般宠爱,只因我是他的功臣。
“闲骑常侍果然是多情种啊。春荣谁不慕?岁寒良独希。我待要跟石友白首同所归!石友却要与姑娘白首同所归啊,哈哈!”我后来认得了这个凑趣调笑的贵客,是朝野出了名的美男子和多情种,潘安。
“到底是石府非凡,不同别家,才养得出这般玲珑的奇女子啊!”我后来也认得了这个潘安带来的奴才,是曾经轰我弃我的孙秀。
主人享受这恭维,身心皆醉,飘飘然若仙。我在主人的爱抚怀抱里偷出一只眼来,但见满室香雾氤氲的酒色女色中,漂浮着媚色、卑色、怒色、馋色、喜色……洇染成一片人间的苍茫,一一落入我眼底。好生无趣。
我心愀然。12
“诸位有所不知,她就是石某最喜欢的女人,石某的第一宠姬、第一美姬。”主人乘兴高声宣布。换来一片恰如其分的叫好和惊叹。主人紧了紧我,伏在我耳边笑问:“美人儿,你叫什么?”
我且愤且悲,扭头不答。却在一刹那瞥到了莞儿的眼神。她分明羡慕地望着我,却是服气的。见我望她,她忙忙地悄然点头笑笑,是祝福的意思。或许我在她眼里,已经是主人的“第一宠姬”,金谷别馆的“第一美姬”了。再环视四周的侍女,竟个个如莞儿一样的眼神,热烈地巴巴望定我。她们的眼睛传给我的意思都是一样的——
第一宠姬。第一美姬。
那一瞬间我即彻明,原来人间便是大舞台,人生就是一场戏,不唯才艺、不唯技能,便是一言一行、一颦一笑,便是整个整个的人生,都在朗朗日月、昭昭众人眼中上演。美貌要人赏、诗画要人品、文章要人读、寂寥要人慰、喜乐要人分。离了他人,谁能自处?但凡那些夸海口说活着但作自己的人,那个“自己”的标准,到底也是参照旁人的标准定的。谁真的能独然生出一个世界来?每个人都活在别人眼里,千秋万代后,人还活在别人的嘴里,任意褒贬评价。
心意如此骤然一转,我释然了。有这么多人巴巴地看着,我就要活给她们看。一如主人,不仅化巨资、美食、绝色为道具,而且要用一生来演一场豪门盛筵,奢靡骄恣的福禄寿喜四全戏,活给客人们看,给天下人看。我如今成了主人人生戏的配角,第一配角。我从深山而来,原是为了给自己的人生戏找最好的观众、最多的观众。把自己的人生化作戏,演进别人的眼、别人的心,这就是我的一生了。如今挣得了舞台,观众且多且雅,我必要把我的戏份演好,必要让众人都看我,注意我,喜欢我,追随我,唯有这样,我才不枉此生。
我和主人间,从此没有爱恨恩怨,我们是同台的戏子,要通力演好这场嫉杀天下人的宴间艳戏。
“我是大人一年前从玉林带来的。”我敛了受伤的情绪,低声温婉答主人。
他在狐疑间静默了片刻,突然大喜而高声笑道:“啊——我想起来了,你就是绿萝屯的野丫头绿珠。是不是?哈!绿珠!”
我无师自通地知道接下来的戏该如何演,我一扭身子,薄嗔道:“你只管绿珠绿珠地叫,我却不知道你的名字。”
他坏笑,耳语道:“我叫齐奴。”
我假意地怒,媚态横生:“你明明姓石,是石崇石大人,却还骗我!”
他大笑:“知道了还问?原来你骗我在先。宝贝,石大人是下人叫的,到了你怀里,我可不就是齐奴了?你说,我是不是最宠你了……”
我承欢、承恩、承情,自然妖娆、妖冶、妖靡。众人看着石君侯佳人在抱,眼里纷纷冒出火喷出烟来,烟熏火燎得我泪流。
席间一场戏,恩爱缠绵,人生更是一场戏,仁义忠孝。其间多少真情假意、虚鸾假凤,有真动了情反而拙劣的,也有演技高超扮得真像的,谁又分得清?
如果人生是戏,谁又是编戏排戏的人?难不成是造化弄人?难不成是人和人,互相为彼此编戏?难不成,是自编自演、自作自受?
我的戏,由谁定?
我亦不解,好端端的,我为什么就要活给他人看?在山里做我自己,不好么?
是的,不好,不好。做深山里的太婆,一生怎么值,怎么甘!
可在这里,辛辛苦苦地扮戏给他人看,莫非又好了?也不好,也不好。
什么才是好?我泪流满面。13
自那日起,我名满京城。我的艳名,添了石君侯的豪名,石君侯的豪名,又助了我的艳名。惹得天下人垂涎欲滴。我们是对好搭档,在人间大舞台上惺惺相惜,配合默契,惹红了天下人的眼,再把自己浸泡在这份眼红里,让自己更红。
单为了这一份红,也值得风光无限地活一场了,便是丢了自己,又何妨?我早已不记得山林间那清淡的懊恼曲和孤雅的昭君舞,我知道每日里来的是什么客人,他们喜欢什么歌舞,我能让不同的客人同样地惊艳和叹服,除了我自己。
歌舞成了职业,成了习惯,不再是我心的快乐所在。但我不在乎,我有了另一个快乐的源泉,就是别人的眼光。
眼里有太多的内容,客人的惊艳,女友的惊羡,仆从的敬畏,主人的宠肆。目光能凝成尊贵和骄纵,它是一出好戏最不能少的部分。不可动摇。
那日伺寝出来,东方已泛白。听说金笛老娘病了,我残着淡妆,转道去看她。从胭脂池沿小石径转上操手游廊,在宝瓶门上台阶时,斜剌里突然荡出个人来,周身花花绿绿的,笑得亦荤荤素素的,险些撞到我,原来后面有个半坦前胸的儿郎在追逐。前面排路掌灯的丫头立时喝骂道:“那来的粗野贱人,看冲撞了姑娘!”
儿郎见有变故,转身溜滑得无影,后面的小厮拥上前,只拧住了那俗陋女子,要拖出去打。那女子显见的没经过这架势,一身的浪荡风骚片刻散尽,软得跪在泥地里求饶,有谁听?
旁边有小厮在我耳边低声求情:“姑娘,这贱人固然可恶可鄙,不过她在下席也是红人。姑娘大人不计小人过,发发善心,给她留些儿颜面,也不至于污了姑娘的清贵。”
我自恃骄纵,向来目无下尘的,那日照例素面向天,不让视线落泥淖。饶便饶吧,我不介意的。我一举手能让君侯笑,一投足能令下人惧,莞尔也算上席的红人,前日,我一句话便能废她莞尔的艺名,让她重新用闺名宋袆,平日听到她曲有误,也免不了呵骂面斥,对宋袆尚且如此,又何苦计较一个粗俗下席女来?
被释的女子以额触地,叩谢不已。我急着去老娘的病榻前请安问候,不理会地昂然而过。裙裾飘飞,险些拂过她的脸,丫头们怕那张脏脸污了我衣角,忙用脚蹬开她去。
老娘一生未嫁,去世前把她的金质玉笛留给我,嘱我隐退。我没有听她的,但也没负她,此后“金笛绿珠”的名号,成了石君侯的标签,我如日中天,吸尽天下人的视线。只可惜,别人的北京白癜风医院哪家治疗最好白癜风药膏
转载请注明:http://www.dongyamedia.com/yzpp/567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