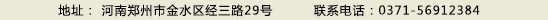胭脂合欢丨公子红妆
公子红妆文/十六青泱它从心底卑微地去渴望,渴望体会痛苦,渴望知道喜乐,渴望能够用心去热爱一个人。(一)万物皆有灵,剑有剑灵,花有花魄。即使是字,亦有灵性。而它于雪山断崖而生,懵懂无知,甚至不知道自己是由哪一句话诞生,因此无法寄生在别人的话语中,也无法托生于书本,无形无体,只能在人间飘飘荡荡。它不甘心,上百年来在人间蒙头乱闯,却只闹出了一段段鬼话怪谈。而奇妙的是,只是街角的匆匆一瞥,却在它黑白的世界里定格住了一个永恒的模样,心中如何都挥他不去,它心头焦灼了数日,再次钻进他半开的窗门想再偷瞧他一眼,他穿着一身素白衫,笔尖下的墨色在纸上如细水般流淌。它心头颤动,哎呀呀,他就在我的眼前,他的鼻尖好似能碰着我的鼻尖,他的体温好似能灼伤我的灵魂。它痴迷地伸出指尖,只想轻轻触摸…没想那书生忽然抬头,那无焦距的眼神一下定在它身上,就似定牢了一般,笑道:"姑娘近日可好?"它一声惊呼,无形的身体穿过半开的窗户跌了出去,慌乱间看见书生打开窗户笑道:"你便是那日清晨,在我书社前哀叹的姑娘吧?"它的脑袋一片空白,准备了多少日月的词竟然一个也想不起来,只愣愣地看着书生从房中出来道:"小生年幼因病失明,因得听力敏锐,记得姑娘的声音,若不嫌弃,今日院中三醉芙蓉花开正盛,姑娘可在鄙院中小坐,赏花品茗?"它有点不敢相信,那一刻它的心好似要融化了一般,轻飘飘地,好似要被四面八方的风吹得一干二净。时至如今的它想起当时,才知那些时日,才是它真正向往的东西,也是它寻寻觅觅这几年,亲手丢掉的东西。此后,它总是找出好多理由来找他,从书文到绘画,茶道至乐理。书生也并不介意,有意无意总会将大门留出一条缝隙,或是多栽了几株颜色瑰丽的花朵,即使他看不见,人们说书生好像变了个人似的,变得爱说话,也更快乐了,他每日迈着轻快的脚步摆纸卖字,日出月落,不知疲倦,总是自个儿说话,好似有人应着他似的。人们议论纷纷,狐疑书生是被妖怪迷了心智。有时它怕别人怀疑,书生在街头卖字时的它只悄悄看着不说话,却好似都能被他瞧出来,他的嘴角总是冲着它勾起,对着空气似得,说着邻里间的胡话,它一个没忍住笑了出来,却被他抓了个正着:"你果然在这。"他的声音温文尔雅,似兰香般沁人心脾,羞得它语无伦次。绵绵韶光,公子红妆,这个秋季竟过得如此绵长亦如此短暂。每到闲时,书生抚琴树下,它总爱坐在树桠上,学着戏子的唱道:"有美人兮,见之不忘,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凤飞翱翔兮,四海求凰。无奈佳人兮,不在东墙。"琴声袅袅,歌声寥寥,薄叶窸窣,清气渺然。它望着书生,书生好似也在望着它,有很多时候它觉得书生才是那个看的见世界的人,而且比任何人,都看的仔细与热枕。(二)低头从城隍庙出来,她慌慌张张地绕出了纷沓而至的人群。直等到了一个安静的小道上,才敢慢慢放下脚步,刚才在庙里被那蛮横的少年踩伤的脚,现在还在火辣辣地疼。可她却没什么心思顾着这个,只从怀里慢慢地捧出一裹东西,摸开帕子,只看见里面躺着一条风流的菩提细珠,脸上顿时飞上了胭脂红,心里扑腾扑腾地。小道上人迹罕至,而这时正值春季,迎春粉黄,海棠嫣红。她合上帕子,对着手心,痴痴地笑起来。能来雀阁的都不是什么寻常之辈,且不说这门口挂着的类似非豪门望族不迎的几大告示,只说这里头的花费,就算是富贵人家,白日里金银满箱地来,夜里穿着裤衩灰溜溜走的也不在少数。那日的天气不是很好,阴雨绵绵,整个建城好似染上了墨一般。她合上窗户,顿时雀阁里头莺歌燕舞的声响就又充斥了整个房间,她如往常一样,捧着自己的琵琶,默默地坐进戏台旁,那乐师堆里头去,把自己藏在那鼓后头,平日里穿惯了布裙,今日管戏台的容妈非让穿了身红绸衣,只觉得台下的目光灼灼逼人,一场戏下来,不知弹错了多少。戏毕,台下欢呼雀跃,台上人最期待的环节来了。在角儿谢幕的时候,台下观众照例要扔花,彩绢上台,在雀阁却不同,若不是白珠子玉石头,都没脸面往台上扔。五十珠,一百银的叫声是此起彼伏,台上是如落雪般地洒满了金银珠宝。她深深地埋着头,脑子中忽然间想起了阿妈临死前的话,狼,往往锦衣华袍。心中便一阵激灵,只觉地在台上是坐如针毡,那上头的灯笼亮的好似要烧着了一般。一声清脆的鼓声吓地她抬起头,只看见一个金角子击在她身边的鼓上。鼓师忙捡了起来,继而又一颗金角子飞来,正砸在她的脚上,她吓地忙收了脚,那鼓师见她没反应,迅速捡了那金角子去。她心里忙安慰自己道,这定是扔歪了。没想又飞来一金角子,正砸在她的琵琶弦上,砰一声弦断。她惊恐地抬起头,目光正对上了台下射来的那一道似狼般的眼神,她瞧见那沈二公子拿起一颗金角子,对着她戏谑一笑,那金角子猛然飞来,正中了她的肩头,她吓得一声惊呼,抱着琵琶,连滚带爬地跌下台。合上房门,还能感觉到那逼人的恐惧穿透门板,直扎心来。过不上多久,容妈就来了,让她去席上奏曲。她跪着求容妈放过她,可没想容妈说不是那个沈二公子,是李家那个三公子,你刚下台那头就差人来请了。她心中虽是安了不少,却仍旧忐忑,但却不得法子,只能修好了琴弦,抱着琵琶,去了席上。虽说是席,没想竟只有李三公子一人,她坐在帘后,颤声问公子要什么曲子听。那李奕也是特别,没直接说曲,倒是把方才的戏评了一评,说湘妃怨是哀怨缠绵,常人在湘妃吟诗时都是用哀乐来衬,没想这这戏的哀乐后头之,竟遥遥地传来了轻快的琵琶曲声,衬着这湘妃怨词愈加幽怨呜咽。那琵琶音似明似灭,就似那情郎遥遥不及之感。听到这里,她心里头微微悸动,他与那些人不同,他是真来听曲的。那晚他们谈论了许多曲子,没想那李奕竟然也是一个懂乐之人,她开心地笑了,不只因为她找到了知己,还因为他让她知道了,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人是懂她,欣赏她的。他把手腕上的东西褪了下来,穿过帘子放在她的前头,那是一串菩提细珠,颗颗风流。他站在帘后对她道:"姑娘才情异人,李奕如遇故人,今赠姑娘菩提细珠一串,愿姑娘不为世俗杂事所累,自在而活。"她透过帘子悄悄地望了他一眼,不经意间竟痴傻了,不知是因为那珠子,还是因为人。那夜,她没入眠,痴痴地想了一夜。而后的日子,在容妈的嘴里就是,那李三公子没来,这丫头就犯痴傻疯,整日坐在窗台上弹琵琶,就似那望夫石似的。来了就更不得了,非把所有人都闹的和她一起疯。女大了就是不中留,看着过不久,不是喜事就是伤心事咯。那夜李奕没有来,她坐乱不安了一宿,到了夜深才知道竟然是在巷子里遭了偷袭,街坊里都传言了起来,说是李三公子和沈家二公子因为一个琵琶女闹了矛盾,二公子每每要点那雀阁的琵琶女,都先被李奕占去,积愤在心,就遣人在巷子里揍了他一顿。第二日才被人发现救了回去,不知是死是活。她彻底慌了神,跪在他府前希望看他一眼,却被门卫给哄了出去。她握着那菩提上了城隍庙,跪在城隍姥爷脚下,一跪竟是跪了一个晚上,城隍姥爷,跪在你脚下的人千千万万,求您看我一眼,民女一生没有做什么大善事,无德无能求您保佑我,只求您护李奕周全,所有的苦难便叫我承受吧。求求您了,叫我承受吧…清晨她被人群惊醒,一个蛮横的少年几乎踩断了她的脚,她听到有人说,那李三公子竟然挨过来了,她听得恍恍惚惚,不只云里雾里地跑出了城隍庙,钻进一条小道,打开手帕看见那条菩提细珠时,才真正清醒过来,他没事了,他没事了!哈哈哈,哈哈哈。她欢呼雀跃起来,好似一个未长大的女孩。一群小孩子看见了这个女孩,嬉笑地唱着歌谣围着她转圈,傻大姑,带红花,上花轿,掉了花帕又丢帽!那女孩子却不恼怒,也跟着他们唱起来,孩子看见了那女孩手上有一串好看的链子,伸手去抢,没想那珠子脱手飞到了山下去。孩子们面面相觑,正打算逃跑,没想到那女孩一跃,竟随着珠子跳了下去,那红色的衣袂绽放,好似火中的血莲花。夜深,容妈打开门,看见她衣衫褴褛地站在门口,发丝凌乱,身上没有一块好的地方,而她的眼睛却熠熠生辉,手里紧紧攥着那菩提细珠,见着容妈,呵呵地笑起来:“珠子…没事,太好了。”容妈看着,泪水不禁流了下来。这便是劫啊~(三)它立在枝头,清楚地瞧见墙外闹哄哄地挤着一帮人,里头有个穿着红袄子的女孩,它认得这个女孩,她生的十分俊俏,一双大眼忽闪忽闪的。昨日她就是拿着这美丽的大眼睛含情脉脉地瞧着书生,问着什么倾心与否的话。在一旁的它心里犹如火烧一般难受,那女孩桃花般的面孔让它醋意翻腾,一激动,着了魔似得喊出声来,吓的那女孩面容失色,大呼妖怪,仓皇而逃。而今那外头熙熙攘攘的,只听道:“孩子,你就听着老伯一声劝,你屋里头定有只话皮子,那话皮子通人性,会人语,迷惑人心,孩子你开开门,让大法师进里头收妖。”它直盯着书生,心头好似被勒紧了一般,只见书生将门插上道:“蒋伯,她不是妖。”蒋伯痛心道:“孩子你别犯傻了,这几日你那迷失心智的样子我们大家都看见了,昨日菁儿还亲眼瞧见了那只话皮子,在你身上打转啊!”书生眉头轻皱:"蒋伯,我向来不信什么怪力乱神之说,她是一个清白家的姑娘,不要玷污了她的名声。""清白?呵,那你可知她姓甚名甚,家住何方,面容长相,身家背景,孩子啊,你说说看呐,她何来清白!"书生哑声失语。它的心犹如冰锥般寒冷疼痛,这句话像一条带刺的小蛇,钻进它的心里,她何来清白…对,我何来清白,不过是一个灵体,没来没由。可归根结底,这清白本就不清白。它还没敲开门,书生便已将门打开了:"你来了?""我…你怎么知道是我。"它不敢直视书生的脸。"因为是你,所以我知道。"书生和往常一般笑着:"就似今晨,我也知道你在。"它虽不知难过为何物,心头却是阵阵疼痛:"你也疑我?""不,我只是突然觉得我是如此不了解你,今晨我想起你时,竟然只能想起一种感觉,却再无其他。"书生伸出手,脸上竟是它从未见过的悲戚:"我甚至,不知道你的温度,你是高是矮,是胖是瘦…"书生一步步向前,它却惊恐地连连倒退,心中浪涛翻天,悲痛欲绝。你可知啊,我如何说地出口,说我无形无体,不过仅靠执念维持灵体,我多么想握住你的手,告诉你我的体温我的心,可…可我却真如他们所说…是一只妖孽而已。书生缓缓垂下手道:"我好怕,我好怕你只不过是我的幻想而已。""傻瓜!"它强忍着心头滴血般的痛,视线穿透过围墙,瞧着路上来往人群的五官,强笑道:"我呀,大约你肩头那么高,嗯,鹅蛋脸,远山眉,小蒜鼻…"它一面将看到的路人五官一一拼凑,一面盯着书生,好似要将他烙进自己的眼睛一般,它看着书生渐渐笑了,自己竟整个人酸楚起来,好似有些个冰凉的液体要夺眶而出,它的视线模糊了,它眨了眨眼睛,像自己真的有一双眼睛似的了:"和一双内下外上杏仁眼。"它的心底涌起一股磐石般坚韧的信念,我要修成人,修成所说的模样:"你记住,永生永世都不要忘却我的样子。""我记住了。"书生笑道,眼眸好似被点亮了一般熠熠生辉。书生确实记住了,永生永世都没有忘怀,而这记住了,竟才是这劫的开始。一拳下去,书生倒在地上,红黑色的液体从他的脸上流下来,它扑上去想捂住血,可血如小溪流一样,穿过它的手掌滴流了下去。那些从草垛里突然窜出的蛮子哈哈大笑起来:"这穷酸书生还挺耐打的!"它愤怒地转过头去瞪着那些土匪,却听见书生道:"你快跑,快回村里去!"蛮子们愣着眼瞧了瞧四周:"他奶奶的,这小子和谁说话呢,今是遇见个傻子了吧?喂喂,傻子,大哥就和你说清楚了,你乖乖把钱交出了,我们就不打你了,听懂了没?""我实在没钱,各位就不要再为难我们了。""笑话,乞丐还有仨铜板呢!"那蛮子大笑得推开书生,一把夺了他的背篮,往里头捣鼓了一番只找出了一幅画,戏谑道:"哟,这傻子还不傻,包里偷藏了一张女人画,鹅蛋脸,小蒜鼻的,长得还蛮灵动的嘛,哪儿的女人,也给我哥几个戏耍戏耍。"书生听后一个激灵,一下挡在它前头吼道:"你们这几个衣冠禽兽的畜生,不要伤害她。"那蛮子们一股火气直冲脑门:"格老子的,找死你!"几个人围上来,拳头就像雨点一样砸下来,它惊恐得抱住书生,可那拳头穿过了它的身体打在了他的胸膛,它心如刀绞,它发疯了一样对着土匪们推打撕咬,可它无论如何都打不着:"你们滚,不要打他,你们滚啊!"书生的鲜血从他的嘴里涌出来,他蜷着身子叫道:"你快走不要管我,走啊!""我不要,我不要!"它的心好痛,好似和他一样也冒出了红黑红黑的血,流啊流,连眼睛都染成了那个颜色:"我求求你们啊大哥,不要打他了,他好痛啊,你们不要打他了求求你们了!"书生满脸是血,已经辩不清何处是眼鼻,他却不知为何笑咧开了嘴道:"傻瓜,你快逃,我不会死,死了…我还怎么娶你呢?"。它傻了,那一刻它觉得世间最美的词竟不过如此,它流泪了,那一滴清色的水珠落在书生脸上,溢开看不见了。它的拳头在那一瞬竟突然捣实了,把两个蛮子打出去好远。几个蛮子面面相觑,突然间听到了一个女人凄厉的尖叫,不知是哭是笑,钻进了他们的耳朵,来势汹涌好似要捏破他们的心脏。他们惊恐地撒开腿逃散:"妖怪!"那个刺耳的词语钻进它的耳朵,妖怪,它慢慢倒退开来,看见书生坐了起来,慌乱地四处摸索:"你在哪里,在哪里,不要离开我,你说一句话啊,我听不见你了,你在哪?"它捂着嘴巴,泪水不停地从它眼眶里流下,好似永远也流不完似的。"我听不见你,你在吗,不要走好吗,不要丢下我,不要!"我会回来的,你等我,千万要等我。(四)她的世界很简单,以前只有琵琶,现在只有李奕。别人说她傻,她不生气,戏楼里的女子都傻,只是她们没她傻得明白,总是矜持着那些荒唐的矜持,直到最后,当冰雪一点点同化她的体温时,她还是这么认为。李奕是爱她的,那夜他用手托着她的脸时,眼里是悲伤与热爱,火热热却又深如碧潭。她吻上了他的唇,热泪从她的眼里夺眶而出,她嗅到了他身上酒精和苦杏仁的味道,这个味道就好似撩人的春风,激地她的心烦躁不安。他一翻身,将她压在了身下,这苦杏仁的香味愈加浓烈地涌进她的口腔,顺着脖颈一路向下,他的手灵巧地解开她的衣襟,她微微呻吟,花迷了双眼,脱了骨似得缠上了他的身子,那一刻,她抛弃了她,他也抛弃了他,他们的肉体相互交缠,抚摸吮吸,好似要交融在一起,一夜情迷,颠鸾倒凤。清晨,她睁开眼,见着李奕安静的侧脸,心中竟然是偷到禁果一般窃喜。她悄悄伸出手指,沿着他的鼻梁缓缓而下,碰触到嘴唇时心中突然如触电一般收回了手,想起昨晚,想起了这曼妙的一夜,那股苦杏仁般奇妙的香味让她又喜又臊,她嘻嘻地笑起来,用被子蒙住了脸。夏末秋初,天气渐冷,干冷的空气钻进窗户的隙缝,梦中的她一个激灵。它穿过人流,每一张掠过的人脸都只有黑白两色,它不知道它为何在这里,它看着自己无形的"身体",心中只有一个影子,那好似是一张白纸上描绘的墨色书生,有着如夜色一般平静神秘的双眼。它在人间行走,看遍了世间人们的容貌,不知道行走了多久,它开始渐渐有了一个女人的身躯,一个婀娜柔软的女人,有着无法媲美的倾世容貌。看遍了世间人们的真假之心,它开始渐渐有了一双顾盼生姿的双眸,和忽颦忽喜的姿态。它走着走着,渐渐忘记了自己的初衷,当它获得一颗人类的心时,它恍然发现自己竟已经忘记了那书生的模样。这诺大的世界,它害怕地不知道该去哪儿。她猛地从梦中惊醒,额上是一层细汗,梦中的真实感让她心有余悸,那个修成人形妖精,突然让她无比恐惧。这几日,李奕总是心事重重,偶尔会说些话,大多时候听了曲子就立马离开,她一直没得机会与他讲这个奇异的梦,只觉得倦意一天甚似一天,有时都不知是何时睡去,梦里又忘却了本来的记忆,与它一同喜怒哀乐。一时间,竟分不清自己究竟是她还是它。蓦得一日,它忽然记起了那个书生,就好似一道清凉的光束横贯了全身,它想起了他,想起了一切。它的世界仿佛又有了热情,它跋山涉水,寻着来时的脚印,回到了那个它逃离过的土地。它看见了那个熟悉的大门,看见了院中的三醉芙蓉,它的眼泪溢满眼眶,它看见了他,穿着清水长衫,执着笔,在窗口临摹,眼眸平静灰白,就如初识时一般。她从梦中醒过来,心里头是苦涩的滋味,那只妖精终于想起了它的爱,而这世间又有多少爱是对等的,桌上孤零零地置着琵琶,李奕已经好久没有来过了,她心里坠坠的,生怕自己所惧怕的终究会来。她推开门,看见容妈怜惜悲痛的双眼,忽然间明白了什么。她不顾容妈的阻拦,奔向李府,路人目光闪烁,指指点点。她瞧见了满目的艳红,瞬间头晕目眩,心肝俱裂,那府门上喜庆的红绸和张扬的喜字,就好似一把把锋利的刺刀,扎进她的眼球。她发了疯一般敲锤李府的大门,吼着着李奕的名字,门开了,门卫们冲了出来,蛮横地将她往外哄去,她在隙缝里看见了他,他躲在人群后面,眼神羞愧而憎恨。她脑中猛地醍醐灌顶,一下推开门卫,心中犹如明镜般清亮,明白了这个男人真正的心,她大笑三声,退开步子,消失在了夜色里,原来无论多坚固的爱情,都躲不开世间的颜面二字。(五)红墙绿瓦,芙蓉花开的院子里。那熟悉的麻酥感又爬上了它的心口,它直瞪着书生,泪水溢满了它整个眼眶,痴痴地开口:"你…可还记得我?"书生放下笔,微探出身子,阳光洒在他的眼底,犹如落入了深渊:"姑娘是?"它忙道:"我是…我…是。"它张着口,却怎么也说不出下一个字,那个时候它与书生的世界只有彼此,何曾想过用名字来称呼对方,而今这名字,竟成了荒谬的阻隔,它急切地张着嘴,却害怕地发不出一声,最后竟只能喃喃道:"我…我是我啊。"书生眼神一顿,好似回忆到了什么,它的心一凛,欣喜地探过身去,你记起我了?你说过的,即使我没有声响没有温度甚至没有呼吸你也会知道是我的,你…"娘子,院中有客。"那温柔的呼唤如利剑直扎过我的心,我的双腿死死钉在了地上,好似一尊破败的雕塑,眼看着一个粗衣木钗的女子挑帘而出,置好茶水,从屋中走出,那一连贯的动作,自然而娴熟。我恨恨地瞪着这个趁虚而入的女人,阳光洒在她的脸上,远山眉,小蒜鼻,杏仁眼,却是平凡又舒心的模样。这眉眼好似从千山万水般遥远的记忆深处奔腾而来,呼啸而至,一下砸在我的眼前,我一个踉跄扶住后头的水缸,却看见水缸中倒映出我那倾世的脸庞,忽然间恍然大悟,我一路走来,嘲笑人有眼却形同瞎子,有嘴却装作哑巴,有心却尽是贪嗔痴念,而万万没想到,我早已成为了这一类人。我修炼成了世人所钦慕的模样,却忘记了我真正想要的脸庞。我惨淡一笑,跌坐在缸旁:"原以为是你薄情寡义,没想是我失去了本心,到头来…竟是我负了你。"化作人形的小妖精早已经失去了飞天遁地的本领,它狼狈地夺门而逃,像一个失败者,那可笑的身躯,悲哀的容貌,就像针芒一样扎着它的心。一个怯生生的声音拦住了它,它回头看见那个女人,害怕而纠结地站在那里:"是…是你吧,我一眼就看出来了,你知道吗?和相公在一起的日子简直是上天的恩赐。"她热泪涟涟,却笑颜如花:"那日子美妙地好似三月的春天,不,请听我说完好吗?我不是刻意对你说这些,我只是…很害怕,那天清晨,他浑身是血地在草地上攥住我的手,声声喊着不要走,他摸着我的脸,欣喜地大喊着就是你。我很害怕,因为我知道他喊的不是我,是另一个女人,一个幸运的女人,而我,偷走了她的幸运。我一直恐惧哪一天你会回来,而我又是那么希望见到你。""我失望了,我配不上他。""不…你有着最纯净的灵魂,比任何人的都要纯净,你知道吗?我很快活,谢谢你,我好快活!"这句话就像是一滴水没入了大海,悄无声息,渐渐下沉,而忽然一个燥响,爆炸开来,瞬间海水翻天覆地。我一个激灵,像是瞎子忽然见到了光明,就是这句话,我找到了,这最初令我诞生的句子,我竟然找到了!我终于可以成为了真正的人,一节一节的骨骼咯咯作响,重获新生的力量充满我的全身,我看见了蓝天白云,嗅见了花香鱼臭。我欢呼雀跃,却还来不及开心,一种心如刀绞的痛苦一下打进了我的心,我成为了人,可我却没有了你。我笑靥如花却泪流满面,我听见了那悠远的琴声,穿过我的心肺,架着我,环绕着我,我舞蹈着歌唱:“有美人兮~见之不忘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愿言配德兮~携手相将~不得终飞兮~使我沦亡~使我沦亡,哈哈。”我朝着那白雪皑皑,我跪倒在那雪山之巅,那个诞生我的地方。我长吸一口气,好似要将人间一口吞吐。我终于成为了人,而人类怎么会如此脆弱,失去你的痛苦竟然是如此难以承受,那极致的痛苦与快乐在我心里疯狂揉杂,几乎要将我从内至外地撕开。我眼眶温热,泪流满面,我瞪大了双眼,眼中清凉而又火热:“这人世,不枉一行,我…好快活啊。”一个身影从崖上坠了下去,没了声响。(六)她惊愕地从梦中醒过来,心中仍是回荡着小妖精最后的那一句话,那个从诞生之初就努力修炼为人的小妖精,最后终于修炼成人,却因为人太过脆弱地无法承受失去,而毅然选择了死亡。多么讽刺,可它为何要说它好快活,它何来的快活?看见容妈焦急的面容,她才回过神来,起身宽慰道:"容妈,没事了,我已经想通了。"容妈将信将疑地抚了抚她的碎发,将手中的汤递来:"一天没吃东西,多少先喝点汤。"她刚端起碗,却是止不住地一阵干呕。她难以置信地抬头:“容妈,难道我…”。在容妈惊异的眼睛里,她彻底明白了,她早已将一辈子都给了这个男人。容妈泪水不止,悲道:"这个没心肺的男人啊,真是造孽,造孽!"她忽的起身,冲到桌前,抓起桌上的红贴要撕,她一声喝住了容妈,容妈不甘地将喜帖掷在了桌上,摔门而出。她缓缓起身,觉得腹中中沉甸而又温暖,她小心翼翼地走道桌前,好似怕惊动了什么,一些微妙的情绪在她心里颤抖,她拈起桌上血红色的请柬,摩擦过沙质的纸面,字字墨色掠过她的指尖。她抚了抚腹间,无限的温柔从她眼里流出,孩子,这是他的孩子。世俗带走了他的心,却永远带不走我们的孩子,这个小生命在我的身体的,犹如我的胳膊我的血液,我们呼吸着同一口空气,享受着同一次心跳,你就是我,是上天和那个男人给我的最好的礼物。从此,没有什么能让我们三人分开。她重新开始了生活,她束起了她瀑布般的秀发,用护额遮住了她美丽的额头。她脱下了精巧的绣花鞋,换上了丑陋舒适的宽鞋。她退去了她合体的衣裙,换上了宽松肥大的衣袍。她坐在阳光下缝着小小的衣服,一针一线,无不精巧用心。她抚摸着腹中的孩子,轻吟着曲子,月夜下,那个单薄而又坚强的背影。秋去冬来,大雪纷飞,红绸如织,红灯若血,李府正逢喜事,全家喜气洋洋,门庭若市,往来不绝。李老坐在红木椅上,笑地合不拢嘴,李奕穿着禧红的大袍,迎着宾客一一入座,只听见喜娘一声呼唤,忙去迎了美娇娘进门,红盖头下那羞涩容貌,隐隐若若,他的心头忽然一颤,另一个女子的脸庞挥之不去。他定下心神,重展笑颜,携着新娘往堂上去。此时门前进来一个身影,红绸熠熠,众人皆侧目而去。只见一五官清丽的女子立在门内,手持一素色琵琶,犹若淤泥出莲,周旁寒风猎猎,却好似侵扰不到她半分。她启步往前,几分吃力,凸起的腹部,一下抓住了所有人的视线,雀阁的女人,众人目光厌恶而好奇,灼灼的目光恨不得直剖开那肚子瞧瞧孩子究竟是谁的,而这里又要上演一场怎样的闹剧,众人猜测着,不忍发出窃笑,又清高地退开步子。李三公子的脸一下烧红到耳根,方才的思念烟消云散,又见李老面若紫茄,怒气上头,羞愧难当,夺步到门前严声道:"我邀你本因你我知音一场,没想你竟然会做出未婚先孕这种不知廉耻的事情,你…你赶紧给我出去,晦气!"只见那女子面色煞白,血色全无,怔怔地看了李奕许久,最后惨淡一笑,悲愤地闭上眼。原来我们的孩子在你眼里,竟然是晦气!众人皆以为此事已了,没想那女子却从容地睁开眼,寻了屋内一处坐下,将琵琶置于膝上,十指若葱,嘈嘈切切,琵琶音质灵动,忽如月夜悲泣,忽如银瓶乍破,众人之心无不为之沉浮,曲毕。女子起身,手持琵琶,忽然将其砸向地上,猛然乍声,众人皆惧,却听那女子开口,犹如深山落雪:"钟子期死。"有人说,那女子说完忽然就凭空消失了,又有人说他分明见着那女子变作了一头火红的狐狸,咬了李三公子一口,所以那李奕才会一夜疯癫,痴傻终身。而谁都没法承认,当那女子迈着艰难而又坚定的步子走出门时,人们的心里无不回响着那琵琶的声音,钟子期死,伯牙破弦,不复鼓之。难道她只是为寻觅一个知音,他们闭目挠腮,心痒难耐,雀阁的女人真的如此清白,不,她定是一只妖精,好会迷惑人的妖精。雪山之巅,她将自己埋进雪堆之中,在冰冷的雪花渐渐同化她的体温时,过往的一幕幕如戏曲般在脑海里台台谢幕,孩子的心跳在她的胸间跳跃,那个男人的脸又出现在眼前,她深深一笑,明白了小妖精的那句话,人世无常,旁人诽谤,金银良心,红鸾帐暖,皆是过眼烟云散,公子红妆,到头来,不如快活一场。“我…好快活。”这句话慢慢凝结,栖于自然之中,忽然有一天,它睁开了眼。(完)北京中科医院正规吗北京中科医院正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