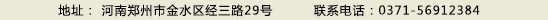孙频东山宴中篇小说专号
我一直想写一个真正的村庄。在我的理解中,不是说写真正的村庄就一定得写农事写方言写牧歌。在我的设想中,这样一个村庄必定是远离文明的,是丑陋的荒凉的甚至是彪悍的,但也一定是最纯真最朴素的。以至于这样一个村庄,在这样一个时代里看过去,竟会像一个装在瓶子里的童话。
小说中的阿德从生下来就是个智障儿,连什么是生什么是死都分不清。就是这样,他还是不顾一切地要为自己找到一点母爱,还是一心想着去另一个世界里寻找自己的母亲。这种对母爱的渴求就是一种他的自我保护机制,因为只有母爱可以让他避开这个世界上的种种凶险。而奶奶白氏拼了命地去保护一个傻孩子,也是因为她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得到过多少爱,而她自己却必须去爱点什么才可以活下去,爱很多时候都可以等同于一种信仰,其力量是惊人的。还有采采这个带着一身邪气的女孩子,因为缺爱,又因为在潜意识里要保护自己,要为自己创造出爱来,所以她会发展出一种癔症。这是她理解中的独特的爱的语言体系。在这个村庄里的每一个人都会用一套自我的体系去保护自己,这几乎是动物性的本能。人比动物多的一件武器便是爱,无论是爱自己还是爱别人,甚至只是去爱一个早已离世的死者。对活着的人来说,都是信仰。
但是这个真正的村庄并不是只有一种动物性的活着,还有对死亡的坦然与平静,这是他们自发生出的哲学方式。生活在这个村庄里的人并不是畏惧死亡,其实他们都是向死而生的。所以我想,这个村庄真正的精神气质不是畏生,也不是畏死,就只是把自己当作时空中的一滴水,一粒沙,平平静静地生老病死。
鲶鱼在这小说里是一种乡村精神的象征和标记,所以村人最后在埋葬白氏之后分食了鲶鱼,代表着她的死亡并不会消解她的宽宥与慈悲。如此一个蛮荒彪悍的村庄,其核里生长的东西却全部是与爱有关的,所有的人都像植物一样,无死无生地生长着,流淌着,只为了能得到一点爱的照耀。这种本质几乎近于透明,近于人类文明史中的童话。当村人坐在东山头上分食那顿鲶鱼宴的时候,人与鲶鱼其实已经无法区分开来。
——孙频
一
若说这水暖村是镶嵌在吕梁山山沟里的一座玲珑塔,一点都不为过。
村子小巧,不过几十户人家,家家住的都是依山势挖出的黄土窑洞。山是竖着长的,他们就竖着挖,结果这几十孔窑洞便一孔摞着一孔,出了自家的窑洞便是站在别人家的屋顶上了。最高的那孔窑洞都快攀爬到山顶了,耸立于众生之上,让人看着都觉得摇摇欲坠,随时会掉下来。
村子小不过是个体积问题,更重要的是内部结构错综复杂而又搭配有致,没有一个人是被浪费掉的,堪比工艺精巧的玲珑塔。张三家的窑洞里住着一男一女过日子,不过这女人本是他嫂嫂,哥哥死后,身为光棍儿的他便继承了哥哥的窑洞和女人。被继承的女人每日照样活得心安理得,若是这小叔子身板不强壮又死在她前面了,而他又碰巧还有个弟弟,那她还会被一路继续继承下去,说不来她活到耄耋之年还要被更小辈的继承。这女人简直就像是张三家的祖传宝物,必得代代相传下去才好,千万不能流到外人家中。李四家的窑洞里住着一个老女人和两个老男人,老女人的孙子管这两个老男人,一个叫爷爷,一个叫小爷爷。小爷爷年近七十,瘦小加老迈,一副随时准备缩回母亲子宫的架势,因为占地面积太小,稍不留意就四下里找不到人了,已经完全蜕化到废物的行列,终日混吃混喝专心等死。
这小爷爷是老女人的第一任丈夫,比女人大出二十岁,女人年轻时候因为吃不上饭而被小爷爷收留。女人四十岁尚且生龙活虎的时候,小爷爷已经提前返祖变成一只满是老年斑的香蕉了,白天不能养活她,晚上不能满足她。后续无援自然让这男人女人都心生恐惧,毕竟还要死皮赖脸地往下活很多年。于是,女人便携夫嫁给了一个四十多岁的老光棍儿。嫁给他的前提是,得养活她前夫直到把他养老送终。人活着哪能没有一点良心,如今把他当爹养老送终也是应该的。她的第二任丈夫欣然允诺,老香蕉已经没有性能力了,要是还能做动,他也一定会无私让出来几宿。独自霸着一个女人有什么意思?难道见个人就举着喇叭宣扬,老子的女人生的孩子可是老子的血亲,血统绝对纯正。又不是皇族,血统不纯则丢了江山,谁的孩子生下来不是在这山里照样吃饭照样干活?那么把自己当人真是要被人捂着嘴笑话。虚荣在这吕梁山里不管用,相反,无趣得很。
两个男人相处甚欢,不忙的黄昏,一人抽一支劣质纸烟坐在枣树下聊天,金色的夕阳包裹着他们,令他们全都面目模糊了,同样佝偻着背,同样叼着一支烟,看上去完全就是亲密无间的兄弟俩。
水暖村的人不好面子只讲实效,难道哥哥遗留下来的女人就坐视不管任其饿死或逼她出去卖淫吗?老婆的前男人老了残了就把他当包袱扔掉吗?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无论日子怎么样艰辛,大家互相搭救一起往下活总比一个人孤零零活着有意思些。再说救人可是积累功德的事,于是水暖村的人人人都觉得自己是闪闪发光的佛陀,不唯有今生,还必定会有修来的璀璨来世,即使死掉那也是上得天堂的。他们对此毫不心虚。于是整个水暖村成了颇为壮观的浮屠塔,在这与世隔绝的深山里自给自足,巍然屹立。
他们不仅善于以各种精巧结构搭伙过日子,还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己作为穷人的才华。吕梁山缺水,水暖村至今吃的都是旱井水,水对他们来说是贵如油的东西。没有水自然就没有鱼,所以鱼对水暖村的人来说堪比贡品。在红白宴上需要上鱼的时候就上条木鱼。看看就算了。两年前王五外出打工,回来的时候带回来几条活鲇鱼。他边流口水边向村民们介绍这鲇鱼肉何等肥美,村民疑惑,比猪肉还好吃?王五不屑于回答,这些山里的鸟人就知道猪肉,却不知道这世上还有鱼肉。他说这鲇鱼不仅肥美,还特别容易饲养,比猪好养多了,还专爱吃粪便和垃圾。他设想如果把它们养在粪池里那简直像给庄稼追了强力肥,不出一年便可肥硕如牛,若过年时把这肥鱼宰了,不仅能省出猪肉,还省了一年的猪饲料。
众人都被这金碧辉煌的前景蛊惑着,前呼后拥来到王五家的粪池边,然后像打发菩萨上天一样虔诚地把几尾鲇鱼放养在臭气熏天的粪池里。村里的厕所都是露天的,粪池终年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所以养个鱼倒也方便,站在粪坑边上就能看到鱼在里面游来游去。微风过处,众人心情都很不错,觉得自己仿佛也是站在湖边观鱼,风雅得很。
这鲇鱼一入粪池便如虎添翼,不过几天就嗖嗖长了两圈,一年下来果然肥硕如猪,加上周身滑腻,一个人都捞不出来。王五吆喝来几个男人帮忙,将粪池里的大鲇鱼捞出,然后洗净粪便,杀鱼架柴生火,炖了一大铁锅鱼肉分与村民们共享。村民们吃完鱼宴后啧啧称奇,这鱼虽说在粪池里靠吃粪便长大,五脏内却没有任何粪臭,肉质鲜美肥腻,真是天外来物。王五的实验大获成功,一时被誉为水暖村的英雄。接着,王五又潜心于在粪池中培植鱼苗,然后隔三岔五将长肥的鲇鱼送于邻里。于是王五的粪池里常年养着几头肥硕的鲇鱼,水妖似的蛰伏着。有客远道而来的时候便捞出来一条宰了待客,至此终于淘汰了祖传了几代的木鱼。
此等盛宴不能不令山外人肃然起敬。
这日,李四家的老香蕉寿终正寝,他早已烂熟,就差这往泥土里的最后一落。一落下去他就会像粒种子一样被种进黄土里,等到再生根发芽的时候就是一个重新开始牙牙学语的婴儿了。众人无不欢喜。一个人能老死是最大的福气,千金难买。他女人送人送到底,极具侠士风骨,虽然一滴泪没有,却还是给死人擦脸理发换寿衣,脸上还擦了两坨浓烈的胭脂,好让这死人看起来容光焕发返老还童。末了,又给已经僵硬的死人嘴里塞上满满一团饭,好让他去了地下也饿不着。
女人的现任男人则给他割好了棺材,棺材上桃红柳绿地画满了山水、花鸟,有菊花有兰花有桃花,看上去金碧辉煌生机盎然,好像人躺进去不是为了入土为安,而是要轰轰烈烈正大光明地开始享受了。水暖村的人喜欢把棺材画得桃红柳绿则是因为,活着时过于沉闷枯燥了。这黄土高原的山沟里,整整半年是冬天,以至于每年春天一看到小草发芽都会让人流泪,觉得总算又活过来了。活着的时候看不到的,只好齐齐都带进棺材里了,活着的人把这些桃红柳绿给死人陪葬上,再看着它们被埋入黄土。最后一缕颜色都被黄土吞没之后,活着的人由衷地在心里笑了,就像看着自己远嫁的女儿在别处享福一样,总算是能心安了。
村里平素没什么可供娱乐的,所以一旦有嫁人死人有红白宴便是全村老小的节日。白宴上,人也埋了,纸也烧了,肥肉和馍馍也吃了,全村人都打着肥肉的饱嗝心满意足地散去了,静等着明天再排出肥肉味的粪便。这气味让他们颇为得意,就像是家家户户刚吞下并消化了一头肥猪似的。何等殷实。
这时候天色已晚,月亮出来了,金黄地卡在黢黑的山顶上,住在山腰上的白氏忽然发现孙子阿德又不在院子里了。这孩子一定又把自己留在坟地里了。他像根钉子一样动辄就钉在坟地里。阿德今年五岁,出生的时候头被挤压了一下,成了半个傻子。平日里别人问他什么,他好像都听不见,湿漉漉的舌头半耷拉在嘴唇上不时舔一下嘴唇,他顽固沉默如一座城堞,薄薄几句语言根本轰炸不了他。可是,这傻子只要一看到往土里埋人,就立刻两眼放光。谁家办丧事往坟地里抬棺材的时候,他一定会第一个闻着气味跟过去,辛勤地像蜜蜂一样一路叮着,跟到坟地里一眼一眼看着棺材埋进去。等到众人都散去了,他还戳在那里不肯走,像坟前的石碑一样肃穆安静,是所有葬礼中最忠实的看客。每次,他站在人堆里,大睁着眼睛,伸长着脖子,嘴半张着,粉色的舌头像狗一样半耷拉出来,一眨不眨地盯着每个葬礼的细节。他表情贪婪狂热地看着这个埋葬死人的过程,就像一个学徒抓住一切时机在偷窥师傅的绝技,一心要早日学到自己手里。
白氏打着手电筒朝山下走去,村庄坐落在东面的山头上,而坟地就在对面的西山头上,虽然站在自家门口就可以与那些坟堆遥遥相望,胳膊长点的似乎一伸手都能把那些坟包像馒头一样摘起来了。可是,望山跑死马,又不能凌空飞过去,她只好一步一步蹙到山脚下,东西两座山头之间有一条山路,这路是水暖村与这个世界的唯一脐带。她穿过山路,再一步步爬上对面的山头。近年来体形愈发臃肿,走一步路全身的赘肉都要晃三晃。
坟地里一片死寂,没有墓碑的坟堆晾晒在月光里分外凄清安静,像一堆没人收留的孤儿聚集于此,摩肩接踵相互取暖。远处黑色的树影无声而阴森地摇摆,似很多鬼影正藏在里面向外窥视。即使作为一个资深的剽悍女人,她也不由得有些恐惧,拿起手电筒朝那黑暗处劈了一刀,黑暗处裂开一道口子,黄色的土和绿色的树像肠子一样从里面翻滚出来。她在坟地里走了几步,又胡乱挥了几刀,果然,几刀之后阿德小小的影子被罩进灯光里了,阿德像石马一样守在一座坟堆前纹丝不动,灯光把他罩进去了他也没有动一下。他背对着她,黑暗的轮廓毛茸茸的,看上去,他就像一个黑暗的末日世界边缘处的守门人,身上带着一缕另一个世界里的诡谲。
她走过去,站在他背后说,阿德,回家吧,该吃晚饭了。阿德对着那扁扁的坟堆老成地叹了口气,忽然犹豫而迟钝地开口了,奶奶,你说妈妈在下面吃饭了吗?眼前这个扁平的坟堆下面埋的是阿德的母亲,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少妇,去年某一天忽然肚子绞痛,然后开始呕吐,没过一天就死了。去年阿德只有四岁,他亲眼看着母亲被装进棺材里,然后棺材像种子一样被埋进了泥土里。当时他并没有流太多的泪,可就是从那时候开始,阿德表现出了对所有葬礼的狂热,他像个牧师一样认真虔诚地把村里一个又一个的死人送到墓地。别人都离去了,他仍然不肯离去,像是要固执地陪伴那些地下的尸体和他们说话,关心他们吃饭了没有。即使没有死人可埋葬的日子里,他也终日一个人在坟地里晃着,像常驻这里的魂魄一般。似乎此处才是他的乐园,别处都不是人间。别人和白氏说,你家阿德是不是被鬼魂跟上了,一个小孩子怎么成天在坟地里玩?也不害怕?
白氏举着电筒,皱着眉头看着眼前的小孩。阿德见没有得到回答,便缓缓转过身来,把脸正对着那束手电光。他那张迟钝的脸看起来像发光的风筝一样浮动在夜色里,见她不说话,他又试探着怯怯地问了一句,奶奶……妈妈在那里吃饭了吗?
自从他母亲死后,每逢吃饭他便要问一句,妈妈在那里吃饭了吗?他不关心任何人的存在,他只关心那个死人。死人没吃他也吃不下。他是真的吃不下。
一次白氏把饭碗使劲往桌子上一墩,厉声说,你妈已经死了,死人不能吃饭。
什么是洗(死)了。
死了就是闭着眼睛躺在那里,不能吃饭不能说话,谁也看不见她,她也看不见别人。
阿德忽然跳起来尖叫着,我能看到她,我看到她就睡在那里,我知道她就在土里睡觉。
白氏一把捉住活蹦乱跳的阿德,朝屁股上猛扇了几巴掌,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再问死人的事。白氏是个强悍粗鲁的老妇人,自打年轻时男人死后就做了寡妇,不是每个女人都有被男人的光棍儿兄弟继承的命运。虽然多年没有男人摸了,但因了土豆的滋养,她的屁股和乳房却剽悍地一路自己长下去,肥硕多汁,对于一个寡妇来说真可惜了这对乳房和这盘屁股。她力大如牛,独自在山上开垦出十八弯的梯田,靠种莜麦种土豆养大了一个儿子。干活的时候她总困惑于怎么搁置这对巨大的乳房,因为它们的广袤和肥硕实在是妨碍了她干活时的大好身手。
情夫倒也有过个把,只是那男人骨瘦如柴还外加肺痨,晚上在炕上根本勒不住她的缰绳,只好任由她在他身上自由发挥。不仅如此,自打被睡过之后,那男人的地也得由她来种,搞得她要对这个瘦猴似的男人从里到外承包了。她被他睡,还要给他种地,就这样,一段时日之后,她听见村里的男人在背后怎么议论她了,那女人既好?菖又像男人一样能吃苦。显然这话是从肺痨嘴里放出来的,如今已经独自成虎成狮满山跑了。她痛恨自己怎么瞎了眼,恨不得把那肺痨一脚踹到山脚下去。自此白氏安心守寡,断绝了再与男人睡觉的心思。奶奶的,就是被猪睡了也不会转身就被卖掉吧。
儿子好不容易娶了媳妇,生了孙子,眼见自己终于熬成别人的婆婆了,还没开始舒畅一天呢,儿媳妇就早早咽气了。儿子三十岁就又恢复成光棍儿了,终日急得上蹿下跳,看见母猪跑过去都两眼发光。留下这么一个孙子真是可怜,早早就没娘了不说,脑子还不灵光,越是看着阿德傻,白氏心里便越是疼。但是她没有流泪的习惯,从年轻时候就戒了,因为留着没用。任何技能长期不用都会荒废的,她难过的时候只会把泪往里倒流,旁人甭想看到她的一滴泪。她用更流畅更熟悉的身手来掩饰自己的疼痛,比如现在把阿德抓起来粗暴地打一顿。
打过两次之后,阿德果然问得没有以前那么频繁了,可是他并没有善罢甘休,他终日观察着她的脸色,捕捉着她脸上乍现出一丝半缕的晴光,伺机再问。每隔几日,一端起饭碗,阿德的嘴就会娴熟地绕到这个话题上来,那就是关于埋在地下的母亲有没有饭吃的问题。白氏从这堵住,他又会从另一个地方冒出来,简直拦都拦不住。每到这个时候他简直就像一辆上了铁轨的火车,被轨道牵引着,根本无法停下,即使知道哪个站该停他也停不下来。他所有的结论一定会准确无误地庄严肃穆地滑进最终的车站,那就是,他地下的母亲究竟饿着了没。
她看出来了,如果有合适的入口,他一定会钻到地下给他母亲送饭的。不管怎样,这个傻子的悲伤还是让她有些吃惊,她看着他迟钝的脸和半伸出来的舌头,忽然觉得她其实并不真正认识眼前这个小孩。一年前,他母亲去世的时候,他也是木讷的,呆呆的,没有泪。她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的悲伤会一直持续到来年去。而且就是到了来年也没有一点刹闸的迹象,他好像不仅没有淡忘了母亲的模样,相反,母亲像只会自己发电的灯泡一样在他身体里驻扎起来了,时不时就自己发出光来。她透过他的瞳孔都能看见那个死去的女人发出的诡谲的光亮,像荒野上亮着的唯一一点鬼魅的灯火。而这孩子,她忧心忡忡地看着他,他正不顾一切地向这点灯火跑去。他那么渴望去接近它。
现在,站在坟地里,阿德又迎面绕到了这个百问不厌的问题上,这简直是一座可怖而坚硬的礁石,似乎只要出海就一定会迎头撞上去。尽管他小心翼翼地怯生生地拎出这个问题,白氏还是生气地一把拽住他的衣领,像拎瓶子一样拎起了他,她像晃瓶子里的水一样把他晃了几下,然后大吼,跟我回家。说完便夹着双脚悬空的阿德离开了坟地。
她心虚地看看周围可有人,深更半夜地在坟地里流连不去,让人们还以为他们祖孙俩是合伙来盗墓的。
二
桌上又是毫无悬念的两碗小米稀饭,一大碗蒸熟的土豆片,土豆片切得敦实有力,一个个都能赛过磨盘,稳稳地盘踞在碗里。就是靠这土豆,山里女人才长出了敦实的屁股和乳房。白氏抡起一块土豆片,蘸了一圈血红的辣椒就往嘴里塞去,土豆片下去了,辣椒酱在嘴唇上落了一圈,像抹了极艳的胭脂,妖媚得很。她吃完两片土豆了,阿德还坐在桌子后面不动。他呆呆坐在灯光下像块煮熟的番薯。白氏敲敲桌子,说,快吃。阿德忽然抬起头偷偷看着她,嘴唇动了动。她生怕他嘴里又说出关于那个死人有没有吃饭的话,连忙去堵他的口,你快吃吧,你妈肯定有饭吃,埋她的时候我在她嘴里塞满了饭,她永远饿不着的。
阿德看着她,眼睛里忽然就储满了泪,泪憋在眼眶里却不往下流,她看得肝肠寸断,她嗓子里一哽,连忙往里又塞了片土豆,好把那哽咽尽快咽下去。阿德的泪转了几圈还是落下来了,他无声地流着泪,忽然大声对她说,你骗我,你就系(是)骗我,妈妈根本没有饭吃,她洗(死)了。
白氏吃惊地看着阿德,她忽然觉得此刻的阿德就像魂灵附体,他身体里似乎获得了一尊崭新的人格,这个人格通透,聪敏,把那个傻子阿德打压下去了。但是她反而更加感到害怕了,就像是,坐在她眼前的并不是阿德。这时候阿德蹒跚着从自己的椅子上跳了下来,走到她面前,又是那么无声地落着泪看着她。他怎么会这么娴熟地用眼泪摧残她?她一边诧异着,一边抱起了他,把他抱在了怀里。他毕竟只是个五岁的小孩子,一个没了娘的孩子总是可怜的。她把他抱紧了,他也把自己扣在她怀里一动不动,尽情抽咽……
……
——摘自中篇小说《东山宴》,作者孙频,原发《花城》
转载请注明:http://www.dongyamedia.com/yzxg/297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