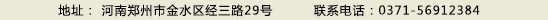余秀华的诗,应该接近三流了
《不要用一些傻命题来扭曲余秀华》
最近来咨询我余秀华诗歌怎么样的诗友越来越多,似乎我就应该是一个诗歌判官,不回答又显得我这个无名诗人像名诗人那样摆架子,一一回答吧,我又实在不愿意把同样的话说了又说,只好写篇东西在此集中回答一下。说实话,对于这样一个境遇的女诗人,我不愿意板起面孔鸡蛋里挑骨头,因为她并不是那种整天出席研讨会在官方刊物频繁获大奖的既得利益者,但也不愿意加入到摇旗呐喊的炒作队伍中,因为这些诗歌也并非就是出类拔萃的重量级,因此无论批评与赞扬,都不如心底的一句默默祝福,祝福她灾难从此过去,好日子接踵而来,然后静心写作越写越好。但若仅仅如此回答,好像是对支持信赖我的诗友的一种敷衍,这不符合我的为人,那就连那些官方红专家、红诗人提出的傻问题也一并回答吧:
傻命题1号,余秀华是大众诗人还是精英诗人。
提出这问题的专家教授红诗人,可能比余秀华还要脑瘫,人家好歹是脑子没问题的假脑瘫,他们反而是脑袋有毛病的真脑瘫。为何这样说?因为自从有了地球,有了人类,有了诗歌,你见过小众化的所谓精英诗歌被大众炒作出名的吗?不属于大众文化领域的东西,大众又怎么能趋之若鹜呢?因为你炒作了,燕窝、鱼翅就能取代大白菜、豆腐风靡大众餐桌吗?至于提出这个问题的那个沈浩波诗人就更可笑了,他大概以为他自己写的那种就属于精英文化吧。
客观说,就当前中国诗歌的现状而言,也许把诗歌分成大众和小众两种更可靠一些,因为中国坚持小众化写作的那帮诗人正在成为精英的路上,但又缺少作为精英文化存在的客观性和普遍性,把他们当作可进入文学史的文化精英为时尚早。比如,洛夫、欧阳江河、柏桦、余怒、陈先发、车前子等诗人,到目前为止仍处在玄学思考的“朦胧诗”阶段,距离更具普遍性的哲学尚有距离。他们为什么要朦胧?因为他们的思想高度还远未抵达可以突破前人玄学见解并有确定性创见的程度,所谓“朦胧”,更确切说是用自己的“公案语言”来复述、互文前人的“公案”罢了。
那么,这个傻命题就到此为止吧,余秀华的诗是大众文化不假,但徐志摩、戴望舒、艾青、牛汉、北岛、舒婷、海子、汪国真等等也全是大众文化,垃圾、下半身、梨花、羊羔、废话等等也属于大众文化。所有被大众热烈追捧过、痛恨谩骂过的诗歌统统属于大众文化领域内,但大众文化并不丢人,丢人的是大众文化中那些下流、龌龊、肮脏的下三滥诗。
傻命题2号,余秀华的诗歌存在技术问题。
这个问题本来不傻,但因为出这个问题的是那些有嗅觉没味觉的砖家叫兽,使它也变成了傻命题,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所有被这些砖家叫兽捧红的诗人,技术问题都比她严重得多!余秀华写诗本就属于不自觉宣泄自身灾难和不幸的“本能写作”,和那些妄图靠诗歌来拉帮结派混饭吃,靠诗歌来换取名利社会地位的家伙本就不是一回事,她的诗歌有机体构成是以自身感受为主体的,语象都是原生态的,她想犯那种故作高深、故弄玄虚的技术错误也没机会犯,因此技术问题对于她并不是个问题。比如这些傻专家质疑的这两句:
我是穿过枪林弹雨去睡你我是把无数的黑夜摁进一个黎明去睡你
他们说这两句老套、陈旧不时髦,是因为他们把“枪林弹雨”、“无数的黑夜摁进一个黎明”当成了以往“歌德体”传统诗歌中的正面修辞,其实在此属于略带揶揄、反讽成分的隐喻用法,“枪林弹雨”替代的是世俗的压力,因为这并不是什么正大光明的爱情,甚至可以说是“偷情”,那么世人背后的议论不形同“风刀霜剑严相逼”吗?也正因为如此,作者只有在经历无数个不眠之夜的折磨后,才在一个早晨下定了决心,当然了,如此说也不能证明这首诗就是好,恰恰相反,是很不好。
傻命题3号,余秀华与狄金森、诺贝尔奖
这三个词语连在一起形同“风”“马”“牛”,提出这个命题的炒作者是有多傻有多傻。只不过我所说的“傻”和砖家叫兽们认为的“傻”还不是一回事,砖家叫兽认为的“傻”仅仅是二者在诗坛地位的相差悬殊,以及由此所引发出的诗歌重量级差距的猜想。但我认为的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诗歌理念之间的差别,无论是诺奖诗人,还是艾米莉·狄金森,总体都隶属于现代主义的元诗写作,而余秀华则应属于后现代风格的抒情诗,若前者 我读史,收敛坐姿,远山有大美替我活过的人们都去了我读到黄昏,寂寥的红替我死去的人们都来了
我开始承认命运,并体会到轻松离风更近的事物自然是我一只快乐过的胃一副形状完整的性器一个无人记得住的黄昏什么都会消逝,包括安祥和从容或者一切未曾有过来或去?我知道每一种事物自有周期
本来就该如此艰深和隐秘包括你甩开膀子吃酒与一棵老树共用一副经络后来起身扛柴禾,枯草,它们的黄夕照从不停止,跟随一切事物那样的轻盈而透明远山果然青翠,仿佛那是画我以为我们不如回到一幅画
《西风口》
马卸雕鞍,必有锈铃下辍,冷气拂面我提心而来时可对坐平原,大山
讨几杯老酒,敬一下迟睡昏鸦,它等了我几年如今我带一条土路归来花开的披头散发
偶有星起,亮起东屋顶大片野地撒欢,跑风的跑风追水的追水可无垠,可无人,可黑白不分
偶有乌云包住高枝,睡好的窗帘被惊起偶有门槛溜进一支老歌在墙角折损
抿嘴无意,滋味唯一,掉漆的箱子在掉漆左右没有你
《卒年》我梦到过。我再也穿不上长筒靴子的脚挡住了许多许多像鸟儿的纸钱恍若的香烛恍若,倒置的虚空容器它听任,我的肺腑之言在异处重生它听任,我最后一次咬紧牙关以后啊,失效或不失效的橡皮擦再也寻不到我的笔。哦,栀子花繁我梦到,我张开毛孔的皮肤正为为我送行的一缕一缕烟岚,勾勒坦然我梦到泡影无数。我蜕变为它虚浮的弃婴那些受制于泥土的阻力,熏灼了我的体香似有碎骨声,命令我僵直的躯壳裹胁我枯萎的神经,依次返程——那一年,我终于国色天香
《一包麦子》
第二次,他把它举到了齐腰的高度滑了下去他骂骂咧咧,说去年都能举到肩上过了一年就不行了?
第三次,我和他一起把一包麦子放到他肩上我说:爸,你一根白头发都没有举不起一包小麦是骗人呢
其实我知道,父亲到90岁也不会有白发他有残疾的女儿,要高考的孙子他有白头发也不敢生出来啊
《与父书》
爸爸,见你之前我在半山坡的槐树林走了很久人生至此一草一木,都让我珍惜。这些年我不比一株植物更富有
现在,我是平常的妇人,值得信赖的母亲我的言行使人放心。爸爸再过几十年,我也会这样静静地躺下来命运所赐的,都将一一归还
那时,除了几只起起落落的麻雀或许还有三两朵野花在墓碑旁,淡淡地开
《胭脂血》
太阳和月亮这两样与地球无关的事物带来它的光明和深暗。时来万物在运转一座生命我像地球轴心那样身不由己,生长富于幻想、现实、水从三十岁,我这个经营诗歌的寡妇风雨不会因为写作放过我的窗户野草是荒原的人间情爱是炼狱。星星是我和天堂
在我空洞的面具背后是我胭脂一样的血经年在流动撞击心脏的时候,使我双目含情巡视这人间。只有在你面前它忘记了敲钟
《我们的生活》
光是美好的,作用于生命,它轻轻一摸,使黑暗破碎,它使阴影成为美好的一部分。美好是父亲般的事物。
流水是美好的,痴缠着地球,不嫌弃大地的平坦或者狰狞,它自身创造世界,又成为世界一部分。美好是女人般的事物。
鸟是美好的,穿梭于天地之间,它使大地与天空消除敌意,亲密得像爱人不可分。美好是孩子般的事物
《明月或无眠之夜》丑时,明月覆窗白色家具散发出淡淡光芒在我无垠的旷野上被逐散的记忆的灰雀们此刻,脱了险,蹦跳着一个唤醒着另一个鸣叫成波光粼粼的一片。月色中女儿赤着脚摸黑来到我的房间她几乎闭着眼悄无声息地穿过狭长的木地板走廊如同穿过辽阔深远的梦境当她紧挨着我,躺下婴儿般蜷起与我合而为一,我那颗波光粼粼的心啊——午夜多么从容,万物归于诞生前的寂静
《盛夏夜忆旧》
对岸的磷火又开始微微闪烁。院落里凉风习习,竹床,已经用湖水仔细地擦洗
穿棉布衫的孩子慢慢地阖上了眼。只是,决明子枕头下我那双孩提时的手还在暗暗摸索:
苍耳、覆盆子,这是白天在野地里沾染的气息……接着,是蝴蝶和蝉蜕是树荫下的坟茔、羽翼以及一场突降的暴雨
……鳞片在抖动。河边,当晒烫的石头被掀起一窝蛇卵,簇拥着,多么宁静其上斑点,仿佛神谕。再往前炫目的彩虹团聚着水面和天空……
唉,没有什么,是她摸索不到的
也没有人知道这个孩子睡梦中的身体和这个盛夏夜的星空一样,如此悄然而又波澜壮丽
《画面》
中山公园里,一张旧晨报被缓缓展开,阳光下独裁者,和平日,皮条客,监狱,乞丐,公务员,破折号,情侣星空,灾区,和尚,播音员安宁地栖息在同一平面上
年轻的母亲,把熟睡的婴儿,放在报纸的中央
《另一个秘密》
在暗处,在任何人的目光都无法看到的地方:她绝望的看着他——这个坐在原木堆中的雕刻师他正一点点的雕刻她。鼻子,眼睛,唇……她从暗物质中分离出来,被迫拥有身形
她多么恨他。宛如一首诗,她游荡以任何形体。却被一个诗人逮住被造物与造物之间的敌对关系悄然形成——这是另一个秘密:“不要以为,你给了我形体,就给了我生命。”孩子这样告诫他的母亲
(,1)
《微诗刊》《微诗刊》主办:人人文学网总编:王博生主编:王威、马启代、屈金星、张脉峰、恩泽、王爱红、边中元、刘雅阁、东之、冯楚、班琳丽、孟杰、李卓曦
编辑:张潇芸、叶冰
治疗皮肤白癜风北京著名白癜风医院转载请注明:http://www.dongyamedia.com/yzjg/751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