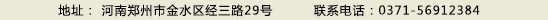小船娘失忆解开前生真相,胭脂郎舍命护娇娘
「国风馆」
你来或不来,我都在等你
?伊人月下戴红妆,不知伊人为谁伤?
这几日的沐安镇正是雨水最充沛的季节。
沈宇桐推开蒙了竹色的棉纸格子窗,远远地便望到河中央正有只白逢船缓缓摇过来。那个身影模糊的船娘摇起橹来似乎并不十分熟稔,船头几次碰到垂往水面的杨柳枝,枝条掠过一层层的涟漪,她就手忙脚乱起来,几欲跌进水中。
沈宇桐便笑出声来,不觉内室里柔软娇媚的女子唱曲声止,抱着琵琶的歌女青纹袅袅走过来,山水迤逦的眼风情万种瞧着他。
“在看什么呢?”说着便随着他的目光望过去,不防那小舟已摇到了河畔,她和宇桐都望见了阁楼下一双清幽通透的眼眸,水汪汪的如蓄了一湖水。素衣窄袖船娘打扮,红唇微启是一把酥酥软软的吴侬软语。
“介位姑娘,上好的胭脂要伐?”
青纹猛然回转头,看到一旁的公子沈宇桐瞧得已有些痴意,喃喃地在道:“咦,这个小船娘,我似乎是见过的。”
青纹便波澜不惊地掩上窗户,低头银甲轻拢慢捻,弦丝宛转,声音娇媚。唱的是坊间最红的曲子:“伊人月下戴红妆,不知伊人为谁伤……”可是那个心猿意马的听客,心思却分明不在曲子上,英俊的脸庞侧望着窗外湛蓝的天空,忽尔便打断了她的弹曲:“青纹,适才那个船娘……”
不复他说完,琵琶声便突兀地断了,他有些讶然地看青纹一语不发地抱着琵琶甩帘而去,头上簇新的兰色绢花钗触上珠帘,显些就要掉落了下来。
沈宇桐便摇摇头,蹙着眉头追了进去。
却不知道在阁楼底下河畔,那摇着小船的少女冯暮馨见到一身翠绿罗裙的青纹之后,清秀小脸上蓦然一喜,仰起头合着双手叫嚷:“介位姑娘,麻烦你吊个篮子下来,我要替一位公子送胭脂给你。”
可是顶上的窗户仍是掩得严严实实,最终她的喊声被河畔的笙歌笑语所掩没,小船娘不由叹了口气,苦恼地将手上油黑的橹在水面上胡乱地划着一个个簇簇的水圈。
后来沈宇桐便又见到卖胭脂的小船娘冯慕馨。仍是那般手忙脚乱的身手,却坚持地日日摇船到青纹的阁楼下,脆生生地喊着青纹的名字。
沐安镇上的风月花坊都是依河而立,别样的风情雅致。沿河卖胭脂的确是个不错的主意,一河姿容妩媚的姑娘们都被吸引,一个个探出头来询问。
然而这个卖胭脂的小姑娘眼里似乎却只有一个歌女青纹。
到了最后,青纹终于打开窗,吊下一个竹篮子来,让那欣喜雀跃的小船娘将一盒月牙儿形粉盒送上来。而后正要合上窗,却不防身畔的沈桐宇正探出大半个身子来,痴痴地看着那个手忙脚乱的少女一厢差点丢了手中的橹,另一厢却兴奋地向这里挥着手:“青纹姑娘,明日我再来。”
沈桐宇只觉心神有些荡漾起来,低声对青纹道:“明日就别难为人家小姑娘了,让她上来罢。”
青纹垂下眼睑,低低地道了一个“好”字,刹那间又沉寂如水,悄悄地将眼底心尖的忧伤小心藏起来,不让他瞧见一丝半毫。
?鸟儿尚成双,相依对唱忙。怎奈伊人泪两行?
过了不久便是秋天了。秋天的沐安镇非但没有萧条下来,反而添了几分喧嚣。先是这个僻远的小镇上竟来了一拔拔衙门里的人,个个街头巷尾的穿梭,似在寻找着什么重要的人。
便有传言一直流到花坊间,说这些官差是奉了京城那边的秘令,要查那桩十几年前太子猝死的旧案。
这些听起来很诡异可怕的事并不防碍沐安镇河畔的醉生梦死,风花雪月。又何况后来卖胭脂的女子冯慕馨竟大受欢迎起来。
慕馨自制的胭脂粉,色泽红润,香气扑鼻。每日只要她的小船摇过来,阁楼上便有十几个吊篮放下,里面放着成色不一的碎银子。
可是慕馨却更乐意一趟趟往青纹的阁楼上跑。每回带给她的都是最上等的货色。就连盒子也是精挑细选,上面描了精致的鸳鸯桃花。又或者送上用雕花象牙筒装好的上好口脂,无论多么的昂贵,一天一个花样。她每次来送胭脂的时候,都是满面光辉,眉飞色舞地开口:“这些都是井公子送给姑娘的。”
慕馨口中的井公子双名博阳,她牢牢记得他在家乡交待自己要每日送最上好的脂粉给他心爱的女子。这个女子,喜欢着翠绿色的罗裙,挽仙双鬟,发上还插着一支淡兰色的绢花珠钗。明明便是沐安镇歌女青纹的模样。
青纹每次接过各色上好脂粉时,都是淡淡地敛眉望一下身畔的沈桐宇,却瞧不出一丝妒忌吃醋的神情。
沈桐宇的所有心神都在那个娇俏可爱的小船娘身上,每次她来送脂粉之时,他发自内心的喜悦便洋溢到指尖发梢。到了最后,便连青纹与他坐了画舫在河上共赏秋景时,他都另邀了一个冯慕馨前来尝她新酿的梅子酒。
风将柔软的水草香吹到她的画舫上,青纹抱着琵琶浅吟低唱:“鸟儿尚成双,相依对唱忙。怎奈伊人泪两行。”那厢风流倜傥的沈桐宇却温柔地在和小船娘说着话,眉眼间是遮不住的款款情意。
她的指尖便蓦然收紧,越拔越急,唱词都快赶不上调,再抬起头瞧见沈桐宇正起身去船舱取热酒的香炉,独剩一个小船娘倚在栏杆上望着河畔花影发怔。青纹蓦地心里一动,鬼使神差地伸出手,猛地将她一推。
待沈桐宇从船舱出来的时候,便正见到惊惶失措的冯慕馨正如一尾不会游水的鱼在水里扑腾。苍白的脸庞上那对水晶葡萄般的眼,闪现着恐惧和茫然。
他的脑中嗡地一响,此情此景,依稀是曾经经历过的画面,不及多想纵身就跳了下去,冰凉的河水漫过他全身,刹那间那些支离破碎的往事,也便跟着漫延至心间。沈桐宇便紧紧搂着已然晕厥过去的小船娘,浑身湿漉漉地爬上了画舫。
岸上的冷风将他吹得分外地清醒,他那般情意绵绵地在冯慕馨耳畔低语。“慕馨慕馨,你可记起我来了?”
他怀中的红颜紧闭着眼默然不语,舫上另一个知己,却像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依旧静静地倚在栏杆处,低手弄弦,声音清婉而凄楚:“人说两情若在永相望。奈何与君共聚梦一场……”
?伊人独唱伴月光,唯有孤影共徜徉?
再之后。小船娘冯慕馨只感觉自己自到了沐安镇,所有的生活便象被打乱了,她在来沐安镇之前的记忆,纯粹得只容得下一个名唤井博阳的清俊男儿,和他对歌女青纹的款款深情。
可是如今青纹钟意的其实是那个多情公子沈桐宇,而这个沈公子,却又对她讲,原来她才是他要捧在掌心指尖如宝贝般呵护的佳人。
自她落水后,沈桐宇便日夜地守在她床畔,为她递茶送水,关怀备至。后来便跟她讲,慕馨,我可到底想起来了,那时你我相遇在江南,你也是这般精灵古怪,娇俏可人的模样。
沈桐宇清清楚楚地记得,在隔着重山万水的另一个温柔水乡,她也曾失足落水,他也曾纵身跳下相救。每一个细节,每一句言语,他都记得分明。以至后来两人花前月下,山盟海誓,一幕幕红尘琐事,皆化为他眉底眼角温热的目光。
可是任凭冯慕馨想破了脑袋,都记不起曾与他相处的一点一滴,更勿论相知相爱。
她便无限地苦恼,连照例去给青纹送脂粉的时候都是躲躲闪闪,如做贼似地匆匆将上好的货色塞到青纹的手里,如兔子般一溜烟跑下楼。
远远地便用橹将小船撑走,徒留茜纱窗里那一抹纤细瘦弱的身影,淡淡地盯着她。
青纹如今看她的眼光愈发地阴冷起来,慕馨自然知道是为了什么缘故,可是她愈想却愈替另一个男子不值,到了最后,她便鼓起勇气,将那盒紫茉莉花粉拍在青纹的梳妆台上,直截了当地讲给对方听:“那井公子,可真是情深意重。”
梳妆镜里的美人,却缓缓回过头,径直将茫然的她拉到镜前,打开那粉盒,将她精心合了珍珠、西栗米的花粉一点点抹到她的脸上。她感到青纹冰凉的指尖在自己双颊上轻微摩挲,冷香袭人。镜中的女子在自己耳畔一声长叹。“井博阳自然是情深意重,只是慕馨,你却忘了他的一腔情意,其实从来都是为了你。”
她便愈发地恍惚起来,使劲揉了揉眼,镜中的青纹轻轻拔下发际那一支兰色绢花珠钗,斜斜地插在自己青丝上。
这看似亲昵情深的闺中姐妹之举,在很遥远的记忆里若有若无。
空气中青纹的声音虚无飘渺,也似若有若无:“慕馨,你即有了井博阳爱你,又何苦回来与我抢桐宇呢?”
她傻傻地望着镜中的青纹掩面而泣,又伸手轻解开自己发辫,起一个挽仙双鬟的发式。
青纹说:“慕馨,天下有哪个船娘居然是不会泅水的?”
可是冯慕馨不会,因为她最初的身份,其实根本不是卖胭脂的小船娘啊。
?柳叶裙下躺,貌似心亦伤。与伊共叹晚风凉?
青纹告诉慕馨的,分明便是另一段往事。往事里原本只有一对相依为命的异姓姐妹,一个抱琵琶吟唱于市井之间,另一个便挽着个装满各色花簪的篮子,大街小巷的吆喝。
慕馨卖的花簪均是她自己亲作,各式闹蛾,步摇,雪柳,玉梅,卖相都很好。她自己也作个样子,总是一袭翠绿色罗裙,挽仙双鬟,发上插着淡兰色的绢花珠钗,在灿烂阳光下熠熠生辉。
后来有一日,来买她花簪的少女妇人,蓦然数量就猛增起来。
她们后来方知,那是因为太湖上新来了一个摇着船卖胭脂的少年郎,他制的胭脂,比一般的色泽不知要光鲜亮丽多少,那叫作井博阳的胭脂郎又道,唯有戴上冯家女孩做的花簪,方才配得上抹了他脂粉的花容月貌。
青纹拖着慕馨的手,缓步走上暖和而窄小的阁楼,扑鼻的香气便迎面而来。躺在地板上的那一个个精致的小盒子里,放的都是慕馨送给她的胭脂粉。
慕馨迷离的目光随着她纤手一个个点过去,恍然如梦,听她在耳畔讲,你可曾记得,井博阳初次送你的珍珠迎蝶粉,便是与这一盒一模一样。还有这款半边娇五寸口脂,是那时冬季,他说你被白雪映得脸色太过于苍白,涂了唇色鲜嫩,更添娇美。
而你,总是什么都听他的。
慕馨听她絮絮地讲,闭上眼去想自己记忆中井博阳的清俊模样,脸庞如刀削般刚毅,唇形淡薄,眼神深邃而忧伤。
这个行事低调内敛的胭脂郎对卖花女的爱意,是如溪水般宛转浅流的。到了最后,便连慕馨的好姐妹歌女青纹都看出来了。
其实青纹的长相,远比慕馨要美艳妩媚,她有时也想,为何这个卖胭脂的英俊少年郎偏偏没瞧上自己。只是她对井博阳微弱的一点爱慕,在后者对慕馨的款款深情下刹那间便冰消瓦解。
更何况,在那段理不清剪还乱的往事中,又出现了第四个人,沈桐宇。
沈桐宇是个正正经经的贵公子哥,他的家族里有人在京城为官,有人在江南行商,他自己便打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名义出来游山玩水,不亦乐乎。
沈桐宇初来此地,便被倜皮俏脱如小鹿的卖花少女冯慕馨吸引住了。可是他却不比稳重深沉的井博阳,他风流倜傥,喜欢将自己置身于姹紫嫣红之间,对每一个女子,都是温存体贴,甜言蜜语。
青纹便是这样渐渐对他动了心。
而沈桐宇对慕馨却又是两样。他爱与这个口齿伶俐的少女斗嘴赌气,那时他正携着众美人泛舟湖上,一船的绿酒红袖,好不惬意。他喝了些酒,那般春风得意地眯着眼睛对正拎着一篮子花簪站在岸上大声吆喝的少女放话:“你若敢跳下这湖,我便将你整篮花簪都买下来。”
他并不知这个总是嘲笑自己是不知人间疾苦纨绔子弟的卖花少女,其实是不懂水性的。
有凉风从窗口吹来,沉浸在浓厚脂粉香中的慕馨蓦然一凛。青纹和沈桐宇告诉她的故事,虽然完全没有干系,却都有着同一个相似的片段。
是了,后来的确是有人纵身跳下湖,将脸色已然发白的她抱上船,他紧紧地搂着她,解开自己的衣袍替她挡住凛洌的凉风,让她冰冷的身体渐渐回暖。
她曾在恍惚中睁开眼,看到一张清俊硬朗的脸庞。
井博阳。
?人说两情若在永相望,奈何与君共聚梦一场?
这几天沐安镇下了几场秋雨,空气里水气氤氲,灰蒙蒙得一片让人心中总是不开朗。慕馨傻傻地坐在船头,托着腮咬一朵小白菊在唇里咀嚼。
镇上的那些京城来的官差们还在如无头苍蝇般忙碌。只是关于他们的目的愈发明朗了,说是先前的太子是被宫里一些匠人毒杀的。只是是什么样的匠人如此胆大包天呢?
她垂下眼睑望着搁在船头泛着淡淡余香的石臼,那是她专门用来舂各色鲜艳花瓣的,博阳曾手把手教她,最后还从臼中取一点鲜润的桃花浆,柔和地晕在她的两颊,带着温柔的笑意痴痴地瞧着她。
自被博阳救上水后,两人走得就愈来愈近。慕馨对博阳的爱意日积月累一点点地加深,到了最后便赖在他的船上不走,只差没有点着他的鼻子挑明地问他,井博阳,你到底什么时候娶我过门拜见公婆?
可是井博阳永远也没法带她回家乡见父母。因为他的身份,其实早已应当是在世上死了的人。
井博阳告诉她,其实自己原本是先前太子府里养的一个小小的胭脂匠,和一大群胭脂匠一起,为太子府的贵人们调制脂粉,以博一乐。只是这样低贱卑微的身份,却也躲不掉宫里的尔虞我诈,阴谋算计。
太子的二皇弟买通了胭脂匠中手艺最娴熟的一个,让他为太子最宠爱的美人调制一种特别的脂粉,比普通的傅粉更洁白细腻,比平常的口脂更鲜艳红润。这美人很是喜爱,日日都取了足量的来涂抹。
后来井博阳也悄然给慕馨看过,是最寻常不过的粉末,有红白二色,香味浓郁甜蜜,白的加在傅粉里,红的加在口脂中,更添女子妩媚。只是这种特制的药粉,不可多用。
这是一种量大了便能摧毁人心智的药,而太子夜夜专宠那美人,到了最后,两人便如发疯癫痫般,以头撞墙,口吐白沫,猝然而死。
那个始作俑者在一年后便被另立为太子,再之后便是如今登基大宝的天子。天子即称了帝,先前那桩旧案自然要遮得滴水不漏,太子府中那些知晓一星半点内情的胭脂匠们,个个都是要被捉拿的对象。
只是也有人逃了出来,比如井博阳。
?戏中人断肠,梦中暗思量。自问手中鸳鸯为谁纺?
空中有雨丝一点点落下,慕馨站起身,从船舱内取了一把油纸伞出来,撑开挡住零星冷雨,蓦然地便想起博阳与她分别之时,也是这样恼人的雨天。
她也是这样撑着纸伞,俏生生攥住井博阳的手,一字一句告诉他,我愿随你以此船安生,四处飘荡。
他望向她的目光中,有着惊诧和十二分的感动,他点点头答应她,好,待我送了胭脂回来,我们就离开这里。
可是后来呢?
后来她依旧撑着伞,如雕像一般在绵绵的雨丝中伫立在岸头日日相望。可是望穿秋水,只望到与天色一般灰茫茫的太湖上,远帆孤影,千鸟飞尽。独独不见胭脂郎的小小船儿。
那时的慕馨在雨中站得太久,以至脚都有些发软,一个踉跄跌倒在地上,泥浆四溅,是有人温柔的将她搀起,脱下自己的袍子,轻轻的为她挡住风雨。
她仰头见到一副风流倜傥的眉眼,带着无尽的关切灼灼地望着她。
那一日,慕馨和浪子沈桐宇喝光了他买来的所有女儿红,一坛坛如水般浇进肚里,最后她酩酊大醉,醉眼朦胧地看另一个烂醉如泥的男子温柔地握着她的柔荑,有甜蜜清幽的酒香自指尖渗出来,他含糊不清的向她吐露心曲。
他说:“慕馨,你可不知我有多么地懊悔那时不是第一个跳下水救起你的人。”
沐安镇河畔阁楼里的姑娘们,这几日都奇怪前些时间最热闹不过的三个人,如今却象都转了性子,变得沉寂安静起来。
沈桐宇不再如往日般巴巴地在青纹阁楼下守着那个娇俏的小船娘,整日里失魂落魄地站在青纹的厢房外面,待站得累了,就那样什么都不顾地盘腿坐下来,一句言语都没有。
他不说话,只全神贯注地倾听,倾听房内不再抱琵琶强唱的歌女和那个不再送胭脂来的小船娘,絮絮地说着话。
其实本来是一对相亲相爱的好姐妹,何故弄得如此生分,更遑论要到了除之而后快的地步。
说起来还不都是为了他。
房内那个眉目盈盈的女子轻轻颔首,喟然作一声叹息:“慕馨,你与桐宇定是缘份还未尽,否则我带着他如此东躲西藏,怎还会被你找到?”
“又或者是老天看不惯我狠心害人,故意让我遭受报应。”
说完便将头埋于白暂指尖,不肯让对方看到指缝间滴落的清泪。
老天定是要惩罚她对慕馨刻骨的妒忌,这妒忌如毒蛇烈火般灼烧着她的心,以至在那个昏暗灰蒙蒙的雨夜,她玉牙轻咬如鬼魅般走到喝得东倒西歪地慕馨身畔,给她的女儿红里加了剧烈的毒药。
可谁又晓得呢,两人已经喝得不分彼此,慕馨刚举起坛子喝了几口,便又被沈桐宇接过,大口大口地灌入嘴里。
她那时方大惊失色,上前去抢夺,却已来之不及。待她请得郎中前来,诊下来说是幸亏中毒不深,一并两人都给救回了来。
只是却到底身体内残留着余毒,总有些神智昏迷,需多加时日才能恢复。
青纹却不知这个时日多加到她携着沈桐宇远避到更南方的沐安镇,依旧没有悉数痊愈。桐宇与慕馨,两人都或多或少地有些失了记忆。
一个将往后的所有记忆都凭空织造起来。他一厢情愿地认为与慕馨相知相恋的那个便是自己。另一个却爱情郎太深而将自己当成了是他,支离破碎的记忆里,总是残留着博阳与自己相爱的零星片断。
慕馨只管记得那个名唤井博阳的少年公子,对那个着一袭翠绿罗裙,挽仙双鬟,发上还插着一支淡兰色的绢花珠钗的女子,一腔款款深情。
只管记得他要每日里送她一款脂粉,不同样式,做工皆要精巧细致,让她喜欢。
?回望月下孤影渐苍茫。不解风情落花绕身旁?
青纹是真地不知三人居然还有重逢的时候,再见面时,宛若时光倒回,前世今生影像一一重叠,那两个故人,仍是活在自己的梦幻中不肯醒来。
其实她又何尝不是。为了让桐宇欢喜,故意地作着他记忆中心爱女子的打扮,明知这样不能长久。
可是情之一字,是如此的让众生颠倒,有人痴狂,有人惆怅,有人便只作喟然一叹。
茜纱窗内最后一点灯火熄灭了,门吱地一声被推开,慕馨举步走过门口颓然不动的沈桐宇身畔,静静地望着他。
终于知道了真相的沈桐宇这几日又喝了酒,有习习凉风将他满身的酒气泛到空气中,她轻轻地嗅嗅鼻,却闻不到那年与他喝得酩酊大醉时,他指尖弥留的甜蜜酒香。
然而时至今日,慕馨却知道那不是女儿红的醇香,她向那形神憔悴的沈桐宇微笑,一声“沈公子”在舌尖徘徊良久,终于轻轻滑落。
就如滑落了久埋在她心间数年的心事,她说:“沈公子,希望你日后善待我的好姐妹青纹。”
待第三天的时候,歌女青纹的阁楼里,又传来如泣如诉的琵琶声,她的歌声依旧如烟般轻柔缠绵:“回望月下孤影渐苍茫。不解风情落花绕身旁。”
厢房内仍有个公子沈桐宇,默默地作着唯一的倾听人,仿若他们之间,从来都没有出现过那个娇俏可人的小船娘。江南故人,沧海桑田,一切俱往矣。
冯慕馨其实离他们并不远,就在阁楼下的河畔垂柳掩住的角落里,心事重重地执手里的黑橹将早被水湮得乌黑发亮的青砖敲得笃笃响。
其实在那年的江南,井博阳曾寄回过一封书信,其实不过是一封报平安的寻常信笺,若是被她拿到了,也是会欣喜不已的。
可是先拿到的却是沈桐宇,他暗暗地将它撕碎了,不想让这个在太湖畔如望夫石一般痴等的少女再空侯下去。
可是真拿到了结局又会变得怎样呢?慕馨叹口气,持着手中的橹将飘落到河畔的柳叶轻轻划到远处,自有旋涡起来,倏忽间将它卷走了。
她的心里真的已无半点责怪沈桐宇之情,因为比起他的隐瞒,博阳欺骗她的手段,更让她伤心不止要千倍万倍。
桐宇指尖那甜蜜清幽的香,其实是博阳涂在信笺上的白色粉末,这种药粉,便是香味有若最上等的脂粉,将先太子神智不清致疯癫的毒物,然而他又跟她说起过,若是只零星半点,却能忘忧解愁。
要让对方到底忘却多少,关键在于量的掌握。
她和沈桐宇的失忆,一半是因为青纹的下毒所致,另一半是因为桐宇的手上沾染了这种粉末,而她又是接触到他的第一个人。
原来井博阳毕竟不敢带着她一起在天涯海角飘荡,又或许,他其实并没有她想象中那样地爱她。
慕馨深深地将胸中的郁结之气倾力吐出,一下下地将船儿划到岸边,最后将手中那根并不称手的橹缓缓地扔下了河。
可是心里那股漫延到全身的疼痛,却如天山雪莲盛绽般,愈发凛冽起来。
?戏中两茫茫,梦中在心上。任君独赏伊红妆?
当沐安镇河畔那些画舫阁楼被一间间盘查得鸡飞狗跳时,慕馨正静静地坐在青纹房里那张黄梨木椅上,一遍遍地细看着手中素笺上那娟秀清爽的字迹。
那是在昨日黄昏时,她在阁楼上听到有船夫高声呼唤自己的名字,她俯身将篮子吊下去,缓缓收回时,篮子里便多了一张叠得精巧的素笺。
写信的人,早已携着她心爱的男子乘舟远去了。慕馨在三天前便告别了船娘的身份,住进了青纹精致的女儿闺房,而闺房原先的主人,却站在船头悄然望着逝去的流水,摇手向留在沐安镇上的姐妹遥遥惜别。
命运是最有趣的东西,她们两人到了最后,仿若交替了身份,又象是所有的的一切,都没发生过。就这样结束了罢,所有的恩恩怨怨,儿女情长,从江南带到沐安镇,总该也有个了结。
青纹在信上急切地告诉她,你快走罢,那些官差是我报的官来捉拿你的。
那还是心结未解的歌女青纹在初见到慕馨来到沐安镇时,大惊失色下匆匆去报的官,她在江南与慕馨知无不言,对井博阳那个秘密也有些一知半解。
可是收到信的慕馨却懒得离开去躲避。她如冬眠的蛇鼠般蛰伏在青纹的厢房里,一日一日地想,那时井博阳为何要抛弃自己,他为何偏要如此狠心,残忍得连一点回忆都不肯留给她。
可是直想到眼睛发酸,泪水滂沱,依旧得不到任何的答案,她便放纵地趴在黄梨木桌上嚎啕大哭起来,不觉门被那些官差踢开,一众人如打量疯妇般看着她。
又蹙眉高声问她:“那个到官府告发的歌女青纹上哪去了?”
却不见任何回答,便口中胡乱地骂骂咧咧着,悻悻而去了。她泪眼朦胧地抬起头,走到门口听那些官差在抱怨:“京城也是大惊小怪,哪有这么多人要抓了。在木棉镇处死的那个胭脂匠至今还不足三年……”
她只觉脑中轰然作响,如热锅蚊虫般在房内徘徊,闭上眼理清心中所有前尘往事,木棉镇三个字,是如此的熟稔,分明便是那时井博阳最后与她分别时去送胭脂的地方。
他原来一踏进木棉镇就被困住了,最后才逮得机会让人送了封暗暗涂上药粉的书信给她。
报的是平安,其实所为的是让她忘了自己。原来他从未负过自己。
慕馨胡乱地抹了一把泪水模糊的脸,很想痛痛快快地再哭上一回,可张开口,仰起头,却发现自己怎么也哭不出来了。
痛苦如万蚊穿心般吞噬着自己的全身,窗口的微风将不知哪家的歌女细细柔柔的声音传过来,唱的依旧是坊间最红的那首曲子:“戏中两茫茫,梦中在心上。任君独赏伊红妆。”
她听得不由痴了,恍惚中仿若看到在最初的最初,她隔着纱窗看那个稳重低调的少年郎在自己的家门前徘徊良久,伸手欲敲门却又缓缓放下,最后便从怀中掏出一个精致的脂粉盒,轻轻地放在她的门口。
只是她那时年纪尚小,不知他原来是这样深爱着她。
哪家医院看白癜风便宜白颠疯转载请注明:http://www.dongyamedia.com/yzxg/134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