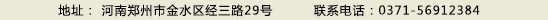散文随笔三街趣事吴林林
三街趣事
吴林林
一九六0年夏秋间,我四岁余,祖母将我送入幼儿园小班。幼儿园在今粮所东仓库,当时叫后府,意即政府后面,两间宽大的平房,是将蒙婆庙改造而成。蒙婆是三街第一美女,蒙姓,家中逼她出嫁,有钱有势的老丑,倩的无钱无势,死都不愿嫁,出家到此庙做尼姑,该庙就叫蒙婆庙。五十年代中间始破败,香火断绝。本人属猴,生性好动、吵事,三天打了五架,武装部王建国政委的夫人孔书珍园长和百色人班主任李老师将我放到芭蕉树下罚站。前两夜刚听过芭蕉精的故事,怕!趁园长与老师不留神,两脚一抹油,翻过矮泥墙,沿粮所外边的小溪跑回了家。
父母上班忙,不管我。祖母次日带我到小学,小学招生已过,一个很老很瘦的老师坐在太师椅上接受插班报名。问:几岁?祖母答:七岁。有吗?老老师戴上老花镜,盯着我,五官后脑看过遍。旁边的樊老师(国民党师长之女,嫁给有三张大学文凭的伪县长李山,随夫到三街,任小学教师)说:这是中学吴校长的仔。老老师收起板脸,笑眯眯道:把右手翻过头顶摸左边耳朵!老师指令不得不听,手一弯,竟摸到耳垂。老老师说:能读书,有官当。朱笔一挥,分到一年级乙班就读。同班有祥万、咪西、阿青大堆街上人。这是我第一次坐火箭,连升三级。
安排前排就座,我很高兴,回头望望,男男女女高过自己半头,不敢找人打。祖母告诉我,老师教什么,你学什么。我不爱听老人言,所以常常吃亏在眼前,但祖母的话,我认为是圣旨,一句顶一万语,赛过最高指示,从来都是言必听、必从。上课铃响,老老师入来,喊:起立!我赶紧跟喊:起立!满堂学生哄笑,老老师脸铁青。正式上课,老老师在讲台上面,手放背后,端坐凳上,高声念:我跟老师这样做,我跟老师这样做。像飞机空姐在做乘机示范。我在下面,也扯开嗓,跟着念:我跟老师这样做,我跟老师这样做。然后昂首挺胸,把双手放在后面屁股上。声音大,动作标准,老老师很喜欢,我挨了表扬。
一连三天,怕大同学打,不敢动也不敢哼,双手背放屁股上,累得发酸。第四天早上,老老师当众给一朵小红花,说这个同学最听话,不吵不闹也不动(其实不敢闹),表扬!同学齐声鼓掌。得表扬,我还怕那个,开始东张西望,做鬼脸,扔纸团。经验老到的老老师板书时一百八十度急转身,逮到恶作剧的我,一把拉到讲台边,书夹里抽出一条三卡长、一寸宽竹戒尺,喝道:伸手出来!看来像吓唬,不怕!伸出手掌。竹尺临空而下,不得了,是真做!赶紧收手,竹尺落空。老老师脱下眼镜,瞄着我,说:戒尺下来能躲过,你是第一个。不再打,撵到最后一排与一高大个漂亮女生同坐。
这个女生,名叫阿仙,陆姓,街上人都叫她仙女,浓眉大眼胖嘟嘟,公主般亮丽,家中的独生女、掌中宝,又是班上的母老虎、夜叉婆。性格刁顽脾气躁,身高体壮臂力大,一语不合,常将男生抱起,举过头顶,掼到地上,再踩上一只脚。我也不敢惹,畏而远之,只能躲,桌子中间划条楚河汉界,一直相安无事。
半年读完,没有长进,再半年读完,仍无长进,老老师不愿带我上“小二”。新“小一”大新籍李老师初为人师,说:中学校长的仔,我要。老老师乐得做顺水人情,也卸下个包袱,我也不愿和母老虎坐,家里也怕我年幼吃力,三国四方,摇头不算点头算,点头一致同意,皆大欢喜。
新学年到,首次成为痾放瓢更的留级生,二读一乙班。那年兴男女同桌,坐在身边的女生,又叫阿仙,但姓陈,个子比上年那个更大,更粗,更漂亮,瞪我一眼,气都不敢出。还常常说娶我回家做上门童养婿,吓得魂飞魄散、屁滚尿流。只好听课。成绩居然突飞猛进,分数一路飙升,上课有问必答,答必对。作业当堂交,想错都难。造的句子,通顺如范文。班里金榜题名,奖状到手,列入好生行列。一日下午,正在玩,被捉来排队,“高小”班的黑美人余杏荣大姐将红旗的一角往我脖子上捆,再令右手举过头顶,如同董存瑞举炸药包,跟着呼“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后,双腮抹上胭脂,推上台,合唱“么什么什嘿,么什么什嘿,放光明哎,么什么什嘿”那首名歌。遂成了全班最后一个少先队员。老老师又不耻下求,来说:跳级到我们班吧。李老师不允,说要重点培养。祖母也高兴,每天上学前,拿出红糖,给舔一下,作为奖励。里里外外都认为五百年出一个了。
新老师为国育才心切,上课前补一下新内容,课间补一下新内容,放学前又补一下新内容。临回家,反反复复叮嘱祖母,这孩子补一补,成材!祖母没文化,不知补什么,每晚饭后补个大红薯,吃得肚胀胃酸多,不停打嗝,半夜痾屁连连。其实已读过一年,炒的是旧饭,轻车熟路,成绩略好,应不足为怪,认为是天才,实在承受不了。一年又一年,一直到“文革”停课闹革命,成绩中等就很满意。上课答非所问,作业乱七八糟,句子狗屁不通,头上“五眼果”是老师给的最佳嘉奖。知识增加不多,脸上、手上、腿上、身上打架留下的伤痕日增,并与时俱进。起初祖母还每天数一数,以便日后报仇、秋后算账。到后来老眼昏花,数不过来,也就不数了。
我家三兄弟,我是老大名叫林林,三街人称之老林。老二山山,老三深深,从后往前读:深山老林。三街人佩服我爸,太有文化了。在三街这个深山老林中,提前预知生三个仔,且名字都安好,虽不如全校长的“新华光明”政治性强,也不如玉家的“勇敢前进”那么有奋发向上的动力,但却实实在在反映了当时当地的现实情况。到文革我改学民,山山改学斌,深深改学进,那是后话。
老三生不足月,体弱,但学习成绩是三兄弟中最好的。老爹就费更多的心让他成为一个文人,继承老爹博学多才的衣钵。从小学始,老三基本都得到任课老师乃至校长的表扬,常常挂在嘴上的就是:隆林将出一个大文豪,中国文人队伍多一个主力,科学院多一个科学家。老三真正争气,他第二,班中没有第一,班中状元的名声,一直到高考前一天才戛然而止。老三是个乖乖仔,不惹是生非,不像他大哥有事无事上门打一架,鼻青脸肿才回家。打架、骂架的事从不会在他身边发生。想不到的是一九七九年高考前一夜,在和最要好,且从小在一个院子长大,在同一个班攻读的同学因为讨论到底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厮打了一场。第二天高考开始,还未回过神来,做题一错再错,鸡和蛋的问题老是在脑中出现,最终两个班中尖子、届中尖子均以一分之差未能金榜题名。
身体瘦弱的他跑到县气象台站做工,想不到的是才短短几个月时间,身体突然拔高、体质突然加强,与高考时判若两人,只等与那位同学再打一场。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年前对越自卫反击开打,部队开始征兵。这年到隆林征的是空军,糊里糊涂和同学跑去报名,招兵排长连考虑都未有考虑,便从同学中把他抽出来,说:这个算一个。新衣服一穿,书生变军人了。出发前的欢迎大会上,又糊里糊涂地被推上主席台,代表一百多新兵讲话。班中状元口才当然没有问题,掌声也自然没有问题,镜头自然也没有问题。
两个哥五大三粗,老二甚至还私改名字叫学兵,都未能去扛烧火棍。倒是最文弱,连体育都不太喜欢(在小学时莫名其妙代表百色队参加了全区的排球比赛,还当了主力。但都是当体育教练的表姐夫拉牛上树的)的老三站到了保家卫国的最前列去。
老三当的是空军,从隆林坐货车,一身灰尘(不是征尘)到百色,从百色坐船到南宁,一路风雨交加。再坐不见天日的闷罐车,也不知道几天几夜,到了首都北京郊外,当空军去了。
表现良好,选到连,再选到营,再选到团,最后到东北的师部去。认为空军部队是开飞机的,却不知四年时间,都是在山里边,别人修飞机跑道,他给修飞机跑道受伤的战友抹一抹红贡。四年空军,连飞机都没见到一架。
解放军陆军,一到部队,手枪,机枪,冲锋轮番训练,我三弟当个兵四年整整没摸过一次枪,没打过一发子弹。倒是老三儿子现在美国留学经济专业,每周都打工赚钱,然后去射击场真枪实弹地打上半天,不知是不是弥补他爸的遗憾。老三服役期满带着一本优秀士兵证,解甲归田。枪没摸到,回来到农业银行里当几个处的处长,天天看人家摸钱。中学五年,千辛万苦,因鸡与蛋考不上大学,回到地方当农业银行的行政处处长,管鸡管蛋,管得领导佩服得五体投地,一个文件上盖上鲜红大印:保送去省外读大学。也不知先有鸡、先有蛋,几年后领回一个大学文凭,金融学位,含金量没得说。优秀大学生,领导奖给了一个金鸡,一个金蛋。工作能力、态度似我爹,优秀共产党员没得说。因为优秀,糊里糊涂中发现自己一夜之间变成了厅级干部。
老二山山,最不爱读书,成绩最好得过第二名,还是倒数的。小时候他爱看打仗的电影,见县中队的兵也排队进场看,以为是这帮兵上电影去打仗的,散场了又见他们排队出场回去,一个没死,很神奇,就立志要当兵,私自跑到户籍办,把名字改成学兵。老妈老爸开通,改就改罢,免得三街人喊阿山和阿三分不清(现在还是有人喊山哥或三哥,两兄弟同时答应)。老妈老爸有文化,亦不忘叫子女学文化的初心,说:音同字不同,叫学斌吧!学斌就一直沿用至今。
改学斌想当兵,几十年过去,连当了官去慰问基层,也没到过军营一次,更何况真正去当兵了。老三想学文,偏偏去当了兵,老二想学武当兵,偏偏一辈子做了文官。
在农村做知青,劳动能力中等,表现中等,像老爹崇尚的中庸之道。农村里表现最好的读大学、当干部去。表现差,村里难管的,当警察、当兵去。表现中中的听话,待着吧!待到邓小平号召恢复高考,已经在民新第七生产队混了四五年,样子差点变成贫下中农,只等村姑她妈来提亲了。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不爱读书的山山一直躲在农村。高考前几天,我爸实在忍不住了,叫我妈步行三十多里跑到生产队把山山抓回来,开出条件:考不考是态度问题,得不得是水平问题。山山就交二毛五分钱领到一张高考准考证。一天也没有复习,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六、十七号从考场上几进几出,试卷乱涂几下交了上去。转眼间,皇榜下来,老二居然榜上有名,虽不是独占鳌头,却也鲤鱼跳了龙门。在小学、中学每逢考试都不可能及格的老二,高考一次过,这年全县参加全国第一次恢复高考才录取十几二十个呢!他的中小学老师眼镜全部跌地,得意门生一个都没有考上,曾经前几名的还考了零分。基本可以肯定,革委会的子弟,分是老师给的。毕业后做了几年中学老师,没做好。想从政,努力罢!在学校从未做过副组长,更不说班长、排长、学生会主席了,直接就当了处长。曾经在德峨公社待过,公社主任、乡长、镇长也只见过,没做过。却去全国第一旅游县——阳朔去当了县长,后来干脆去干了一个正厅长[当地流传:阳朔吴县长(阳朔无县长)其实是吴副县长,听来是阳朔无副县长,都是正的。老三也在藤县当过吴副县长,我也在三江县当过吴副县长,三个县都无副县长,都是正的]。从未当过县市政协委员,在广西区政协常委的位置却有了他的位置。自己本来就是人民,代表自己,最后成了人大代表,还做了自治区人大常委。而且这个人大代表,还是其之前从未去过的河池苏维埃人民选出来的。在学校,在农村,连团员都不是,最多是个少先队员,更遑论党员。不做则已,一做,做到广西一个民主党的副主席,而且还是常务。更想不到的是,还一直做到中央委员。
从政不忘初心,当然还是想当兵。掰着指头算一算,确实超龄了。那去当将军罢。读的不是军校,将军也没份。不过还好,如真做到郭伯雄、徐才厚的位置,也对不起隆林人民,对不起三街老百姓了。倒是老爹有远见,不让他叫学兵,帮他改为学斌,文武斌。别人是学而优则仕,他是学而优则仕,再仕而优则文,又再文而优则画。学而优,文章写得好,屡屡中大奖,上大报。再由《林海雪原》的作者曲波推荐,去做了世界闻名的岭南画派和大风堂的领军人物黄独峰大师的秘书。大师仿佛云游仙人,凡神州世界级景点,轮着去,发誓要画完祖国的山山水水。吴秘书无须天天写讲话稿,大师是广东揭阳人,客家话人家也听不懂,就懒得天天去讲大话。无所事事的吴秘书,天天看大师作画,不久也看出门道,哦!与自己在乡下做知青,在砖坯上乱刻乱画好不到哪里去。每天天将晚,帮大师收拾画具,见砚中尚有余墨,那时不兴浪费,信手在废纸乱涂几笔。大师过来瞄了两眼,说:你读过十年艺院吗?隐藏得真深!我的学生画十几年也没你好!老二窃喜,画画不过如此,开始偷师,此时大师已关门不再收徒,老二只能算关窗弟子,从窗子而入。一路随大师写生,一路将剩墨在残纸上涂鸦。凭曲波老师承认的文学功底,画起来毫无匠气,又得大师率其遍访全国率数名家,技艺大进。从不参加省内活动,待省外一枝红杏猛然出头,省内才大吃一惊,叹为天人下凡。画个山水,大师的山水徒弟转行一批;画个花鸟,大师的花鸟弟子转行一批;还好时间不允,没有连人物一起画,否则今天广西最优秀的人物画大家是否转行去做摄影师也不得而知。至此,中国艺坛多了一个名人,而且是没有进过艺术院校的,却去给艺术院校学生,甚至给在校教授以及院长去上课。一不小心,被国内外七所顶级大学聘为教授。中学教师没做好,只好只做大学教授。等上瘾了,干脆一口气跑到欧洲、美洲,去给英国女王、乌克兰总统、加拿大议长等等,上课去。并和女王一起吃个洋晌午,喝点洋酒,仅差泡点洋妞,挨不挨洋妞泡则有待考究!再到法国罗浮宫摘几块国际金奖牌,同时不忘赚点小费回来,既能养家糊口,又能为国家增点外汇,用外汇给部队增加点什么导弹,等待有一天向火烧圆明园的英法联军报仇雪恨!
此前,为了“搜尽奇峰打草稿”,一路写生,不小心不但走遍神州大地还走到美洲、澳洲、欧洲去。从日本首相开始,几十国元首、议长、酋长都以收藏到他画为荣。此后还传出这些藏家下台后,经济困难,拿画来卖,养家糊口,维持生活。而且相当划算,不用去贪污公款,变成追逃人员。
后来的后来曾有三街闲人问:山山、深深是正副厅级,老林是哪级?有更闲的人答:帮他开车的是正厅山山,坐副驾带路的是副厅深深,坐旁边提包的是准副厅太太,不知省级有此待遇否?!于是三街人互传:可能相当于。
作者简介:吴林林,笔名学民,当代画家、散文家。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画院理事;中国人民政协广西区委会书画院副秘书长;广西区区直文联书画联谊会秘书长。作品分别在北京、台北、香港、澳门及日本、韩国、法国、新加坡、美国、俄罗斯、意大利等展出并获奖。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转载请注明:http://www.dongyamedia.com/yzxg/1390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