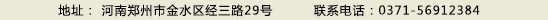龙美文长夜幻歌幽兰露上多多
楔子
这晚春雨迷蒙,如丝如絮,化入风中,沾在行人身上,宛如离人缱绻不舍的目光。此时已近亥时,偌大的西京城空寂无人,昏黄的灯火照亮了光洁的路面。
一个身穿淡青色布裙的小婢女踩水而来,她打着一把油纸伞,淡灰色的伞面上画着一朵瑰丽的紫鸢花。
在雨夜辉光的照耀下,紫鸢栩栩如生,在夜色中摇曳。
但是很快这花便凋落了,少女刚刚拐入一条小巷,就从巷子里传来沉重的闷响,还夹杂着女人压抑的哭叫。
不过半刻,万籁俱寂,街巷中恢复了平静,一把沾血的油纸伞从小巷中滚落而出。
春夜迷离,春雨如丝,别致风雅的鸢尾被浓腥的红花掩盖,红花随濡湿的雨水晕开,在积水之中化为丝丝血线。
一
“这是你画的美人?”位于西京郊外的一处庄园中,身穿花衣的公子抢过了同伴手中的画。
“只是闲暇时打发时间的拙作!”同伴是个圆脸的书生,眼睛清澈明亮,透露着不符合他年纪的青涩单纯。
他也穿了件花衣,却是陈旧的布衣上沾染了油彩,乍一看像是印满了五颜六色的花。
“确实不怎么样。”花衣公子叫皇甫珍,是西京新晋的画师,尤其擅画美人,据说一张图就价值百两纹银。
他啧啧摇头,颇为嫌弃地看着画中那春睡不醒的红衣姝丽。美人云鬓高挽,卧在贵妃榻上,纱衣如烟雾般萦绕着她雪白的娇躯,让人浮想联翩。
“曲宣,不是我说你,你的见识也太短了,如今的美人谁还穿这样式的衣服?还有这环佩明珠,发髻妆容,通通不对!”
“那还请皇甫兄指点一二。”曲宣圆润的脸登时涨得通红,看起来活似个熟透的柿子。
“没什么可指点的,想要卖个高价,就得全部重画。”皇甫珍连声叹息,从衣袋里掏出十几个铜钱放在他的手中,“这钱算是买画钱,凭你的画技,如果不是靠我接济,早晚得在西京城中饿死……”
花衣公子絮絮叨叨地说着,他贫困的朋友低三下四地连连应是,日光在天边敛去光辉,将这对年轻人身影拉得很长。
皇甫珍又在凉亭下坐了一会儿,满脸不耐烦地走了,今晚鸳鸯楼的行首杜小燕跟他有约,他等那妩媚女人的召唤已经等了一个多月,万万不能错过。
“你就继续在这里画美人吧,谁让我们是朋友呢,换个人怎会如此慷慨地借你园子住?”
曲宣只能把头埋得更低,信誓旦旦地说,一定会画更多的画来报答他。确实,穷到他这种程度,能出卖的也只有才华了。
这世上的事就是如此,得到一些,就要付出自己所拥有的。这些道理曲宣都懂,他并不傻,只是运气不好。
于是当天色刚蒙蒙黑,曲宣就扛起一架木梯,直奔两里外的一处荒园。
那荒园不知是哪位富贾心血来潮置下的,装饰好了却并不来住,渐渐满园的奇花异草被荒草淹没,如同美人在风尘中折堕。
但这园中却有他的灵感之源:一朵碗口大的兰花。花瓣洁白如玉,盛放时成蝶形,若放到西京的花市中,估计也价值千金,可是不知为什么却被遗忘在荒野中,从暮春开到初夏,也毫无凋谢的迹象。
“白兰啊白兰,你我何其相似?空有才华和姿容,却只能在这寂寂芳草中度过一生……”他架起梯子爬到墙头,眺望着那夜色中的白兰,在画纸上勾勒出一个女人的侧影。
他是一个穷画师,这辈子也没有见过几个女人,对美女所有的想象都来自于鲜花。皇甫珍深知他的癖好,所以才将他安置在满是奇花异草的郊外。
“牡丹艳丽、茉莉清新、水仙高洁、虞美人热情……”他一边画一边还兀自嘟囔着,似乎真的把兰花当成美人在沟通,“你呢,就是缥缈吧!美人如花隔云端,有距离感的美才是最美,因为人们总是会沉迷于他们自己的臆想……”
他像是个最优秀的话本作者,企图用自己的笔,把所有的看客都兜进迷宫。当他创作之时,脸上稚气尽脱,变得精明而狡黠。
当晚他热情高涨,居然一口气画到了寅时,可是在这一天中最黑暗的时刻,身后突然传来了一阵轻咳。
“咳咳咳……”
这咳嗽声洋溢着浓浓死气,如钝刀般割裂了夜的宁静。
曲宣好奇地回过头,见墙下正站着一位身穿月白色绫纱长袍,头戴黑色纱帽的少年公子。
他明明那样年轻,偏有沧桑表情,眼中藏着虎狼般的光,脸色却又透着病容。
这是身为画师的曲宣,第一次在一个人身上,看到这么多不协调之处。
“我、我是打扰你了吗?”曲宣骑在墙头,不愿下来。
“你是画师?”少年公子看着他手中的草图,饶有意味地扬了扬眉,“我不知道自己的园子中有什么值得你画。”
“抱歉,我不知道这园子是你的,我还以为没有人住……”曲宣立刻大窘,急忙顺着梯子爬下来。
“我也只是偶尔来小住而已。”那少年公子水银般的眸光在他身上转了一圈,又轻咳不已,似有顽疾缠身。
但不知为什么,当被他的目光笼罩时,曲宣有一种连骨头都被拆开了查看的感觉。
“这是你的画?”他咳嗽完了,眼光停在曲宣手中的草图上,“为何画中是美人?”
“因为你的院子里有一株兰花,清雅高洁,我就把它想象成美人画了下来。”曲宣的脸再次红得像个柿子,所幸夜色深沉,替他遮了点羞。
“美人?兰花?”他拿起曲宣的画仔细端详,似乎在琢磨什么,接着他朝曲宣微微一笑,“我叫老头子,不知这位画师,能不能赏脸来园中小坐?”
“在下曲宣!我真的能进这园子里吗?能不能让我仔细看看那朵花?”曲宣立刻欣喜若狂,甚至都忘了追究一位文弱俊逸的少年公子,为什么会起如此奇怪的名字。
当晚曲宣如愿看到了那朵兰花,可是老头子只让他停留在离花朵三尺之外的地方,不许他再接近一分。
可是即便这样,也比坐在更远的墙头看得要清楚多了,他完全不记得主人盛情款待的酒菜,只记得那花瓣细腻的纹路,和如美人唇瓣般红润的花蕊。
而白兰似乎也感知到了他的心意,每有夜风拂过,洁白的花瓣便如鸟翼般微微轻颤,翩然欲飞。
老头子把这一切看在眼底。不知从哪里走出来一个雪肤红唇的黑衣女人,在为他奉上美酒之后,凑到他耳边,低低地说了几句话。
夜风清凉,更深露重,如玉般莹白的花朵,仿佛也听到了这人间的窃窃私语,轻轻地点了点头。
自此之后,曲宣一有空就往老头子的园子里跑,唯一让他觉得奇怪的是,这个名为老头子的年轻人,似乎总是在晚上出现。有一次他带着皇甫珍白日里来拜访,却吃了个闭门羹,害他又被好一番嘲笑。
而皇甫珍依然对他的画嗤之以鼻,却仍要买这幅他新画的美人图。曲宣把这画视为生命,只口中答应,却迟迟不肯完工。
不知为什么,从那株被埋没于荒草的兰花身上,他仿佛看到了知己,那顾影自怜、得不到众人欣赏的美人,何尝不是另一个自己呢?
二
就在曲宣埋头创作美人图之时,老头子的荒园中,来了一位贵客。那是一个身穿紫色罗裙的艳女,皎洁的月光照在她的脸上,将她眼角刻意描绘的紫色眼影映得像是凤凰的羽翼。
女人婀娜地站在月色中,轻轻叩响了荒园的门扉,而与她的妩媚多姿形成对比的,则是她身后那个高大健壮的随从。
随从二十出头,身高丈许,厚厚的嘴唇微微下垂,一双眼睛中闪烁着鹰隼般犀利的光芒,一看就不是等闲之辈。
“你就是龙爷?”园子里响起一阵轻咳,门被打开,露出了老头子年轻俊秀的脸。
“你就是老头子?”龙爷掩嘴娇笑,如花枝迎风,“怎么一点也不老。”
“你也不像个爷呢。”
驱魔师的名字不能为外人所知,一旦被人知道,就有丧命的危险,所以他们大多会取个隐名,以策安全。
而这位紫衣艳女,就是西京城中首屈一指的驱魔师——龙爷,最近她要暂时离京,只能把手头的任务转交给老头子解决。
“‘妒鬼’?是西京城中的鬼怪吗?”老头子跟龙爷坐在荒园中,喝了两口阿朱奉上的热酒,说起了正事。
“不是鬼怪,而是一个人,专门帮西京的贵妇出气的人。他喜欢恶作剧,捉弄那些招蜂引蝶的女人,但只限于调包情信或者剪人裙子之类,从不害人。可是最近却有一位婢女在送信时遇害了,尸体上写了个大大的墨字,衙门怀疑是‘妒鬼’做的,却偏又没有证据,所以才找到我。”
老头子沉吟不语,水银般的眼珠转了又转,他在长夜中宛如一幅蒙尘的画,让人看不清,无法琢磨。
“就帮我这一次嘛,我真的有急事要离开西京,银两我一分不要,全给你。”龙爷像是稚气未脱的小女孩,抱着老头子的手臂撒娇。
最终老头子还是点头答应了,他像是个从久远的时光中踏歌而来的君子,总是无法拒绝女人的请求。
“但是这点银子可能不够。”老头子朝她比了一个巴掌,“我看这事没表面上那么简单,其中必有蹊跷。”
“你这个贪财的老家伙!怪不得大家都不愿意跟你打交道,你就活该独自一个人老死。”龙爷愤怒地大骂。
“既然叫老头子,自会老死。”老头子却不生气,仍笑吟吟的,非常气人。
龙爷拿他毫无办法,喝光了他存的两壶好酒,就带着自己那高大威猛的随从告辞了。这紫衣女郎身影婀娜,仿佛云烟,很快便消失在郊外苍茫的夜色中。
老头子孤身一人坐在荒园中喝酒,夜风吹起了他如月光般浅淡的衣襟,吹得满园的荒草此起彼伏。
而在这空旷寂寞的荒园中,站着一个白衣如雪、伶仃单薄的女孩。
女孩的眼睛黑而亮,像是天上的星光尽数撒落到她的瞳仁中,她定定地望着老头子,小脸上写满了急切。
但老头子仿若没有看到,不徐不疾地喝光了酒,就起身离开了,于是她热情的目光就跟残酒一起慢慢变冷,孤寂而凄凉。
几日来老头子就像是个闲散书生般,每天清晨都摇着折扇,带着眠狼去西京城中闲晃。
他先是去了流言蜚语流传最多的集市和酒肆,很多人在谈论“妒鬼”,女人们都说“妒鬼”性情大变,居然由保护弱者的人,变成了残害美女的怪物。
所有的女人不论是否有姿色,都是一副心惊胆战的样子,连带着胭脂水粉铺的生意也萧条了几分。
他还看到一位花衣公子在书画店外高价兜售自己的画,画上是一位横卧在榻上的红衣美女,冰肌雪肤被烟雾般的轻纱笼罩,若隐若现,引人遐思。
那美人图的笔触他十分熟悉,但画上的印章却是另一个人的。
“皇甫珍又出新作了,这次怎么也能卖二百两银子吧?”两个跟他一起围观的人在讨论。
但是画的成交价,大约比寻常百姓猜想的高很多,因为那花衣公子跟一位大腹便便的中年人走入画社,很快就带着满足的神情离开了,看似收获颇丰。
古往今来,这种把戏他已经见得太多,即便是唐朝画圣,画作也有出自弟子之手的。他看尽热闹,突然想跟曲宣喝两杯酒。
落魄的画家很久没来了,习惯了有人陪伴,一个人的长夜就变得格外漫长。
这晚他特意在西京买了很贵的昆仑觞,端坐在荒园中等待曲宣。可是直至月亮的影子移上中天,他也没看到那位一脸稚气的画家。
他一贯很有耐心,把冷酒烫了又烫,就着夏夜的星光月色自酌自饮,但另一个人就不像他那样沉得住气了。
白衣少女在月色下踟蹰、徘徊的地方正是兰花绽放的所在。
“怎么?想你的画师了?”老头子唇边含笑,轻轻地说。从曲宣提到兰花时,他看到的就并非兰草,而是这个瘦弱的少女。
每次年轻的画师来画画,她都会垂着头,脸色绯红地站在月光下,那时的她娇媚动人,几乎可以把艳丽的阿朱比下去。
“先生,求求你,收下我吧。”女孩再也忍不住了,三步并作两步跑过来,跪在了老头子面前。
“看你这样子也不能打斗,跟着我又是何苦,还不如自由自在地在旷野中漫游。”
“心中有了挂牵,即便能飞翔,也谈不上自由。”她低低地回答,说出的话却比外表成熟许多。
“我可以给你力量,你又能给我什么?”老头子打量着她消瘦的肩膀,枯黄的头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价值。
“我能助先生解决难题。”她眼中闪烁着晶亮的光,“我听到了几日前先生跟客人的对话,‘妒鬼’,注定要死在我手里。”
“哦?”
“而且现在的‘妒鬼’,跟之前恶作剧的‘妒鬼’,根本不是同一个。”
老头子笑了,因为她足够聪明,居然能察觉到这点。之前的“妒鬼”更像个小孩在作弄大人,但是现在这个却以杀人为目的,画在尸体上的墨字,只是为了转移仵作们的注意力而已。
“真是个聪明的孩子,希望我没有看错。”老头子点了点头,他伸出纤长的手指,放到了女孩干裂的唇边,沉吟着说,“以后你就叫幽兰吧。幽兰露,如啼眼,你的眼睛衬得上这样的名字。”
她一口咬住,贪婪地吸吮着那充满魔力的甘甜鲜血,塌陷的双颊如被露水浸润的花瓣般丰盈了起来。
明月悄无声息地将脸藏在了乌云之后,似乎不愿目睹这在长夜中进行了千百次的,人与妖魔的交易。
三
三日后,盛夏的花香被暑气蒸腾,将清冷的寂夜都熏上了几分暧昧的暖香。
曲宣喝得酩酊大醉,跌跌撞撞地来到了老头子的废园中。他并没有回到皇甫珍为他准备的鲜花遍地的庄园,那里的花虽然很美,却像是带刺的美人,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他,他是个寄人篱下之人。
他只想见见那个总是游离世外、很少说话的少年公子,再不济,看看心爱的兰花也好。
门并没有锁,他踏草而入,只见月光下园中酒杯凌乱,一朵莹白如玉的蝴蝶兰,淑女般恬静美好地立在月下。
他看到这遗世独立的花,宛如看到了被世人遗忘的自己。他再也忍不住悲伤,扑到花前,哀号痛哭起来。
“皇甫兄的画又卖了好价钱,为什么我没有这样的才华……”这个大男人泪落如雨,完全忘了老头子的嘱托,双手捧住花瓣,倾诉着自己的压抑,“听说西京外的千福寺重建,要请人再现吴道子的《地狱变》,皇甫兄也获邀尝试,我何时才有这等机遇……”
他哭得撕心裂肺,多年来所受的种种委屈,刹那间如海潮般奔涌而来。
今晚皇甫珍做东,在西京的满意楼大摆筵席,席间这英俊的年轻画师春风得意,风光无限。
同去的画师都忙着巴结他,热情地谈论着《地狱变》这样的恢宏巨作,注定要由皇甫珍这样的青年才俊来完成。
放眼西京,画得又快又好的,除了他还有谁呢?
曲宣像是一只躲在暗处的蛾子,连理他的人都没有一个,如果不是皇甫珍跟他喝了两杯酒,鼓励他继续画美人图的话,估计都没人留意他是否曾来过。
他想起多年来所受的折辱和委屈,悲从中来,扑在地上长哭不起。于是夏日清朗宜人的夜空,都被他的哭声染上几分凄厉的气息。
然而他正哭得伤心,寂夜中一只温软洁白的手,轻轻捧住了他的脸。曲宣愣住了,泪眼蒙眬中,只见如轻纱般曼舞的月光中,正站着一个白衣少女。
女孩很瘦,像是只有十三四岁的模样,但她的眉眼中隐含丽色,尤其是一双黝黑明丽的大眼睛,像是藏着星光的碎片,令人目眩神迷。
“你、你是谁?”曲宣立刻抹干眼泪,惊诧地问。他明明记得自己走进来时,只看到一株兰草,再无其他。
“我叫幽兰。”女孩轻轻凑过头,在他颊边印上了一吻,“你会成功的,相信我!”
曲宣呆了一会儿,“扑通”一声坐在地上。这是他二十几年的人生中,第一次有女人对他示好,即便那人只是个乳臭未干的小丫头,也令他心神荡漾。
“离开这里,抛弃皇甫珍,把你画的那幅兰花美人卖掉,去西京重新开始。”幽兰低低地说,她的声音细而微弱,似乎中气不足,却自有一番振奋人心的力量。
“我、我……”他不敢答应,那意味着他要抛弃现有的一切,重新开始。
“被困在笼子里的鸟,怎么能高飞呢?”幽兰长长地叹息,似乎是为他多舛的命运,也像是为他虚掷的才华。
这声叹息像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探进了曲宣的心底。他仿佛被妖魔蛊惑,几乎在刹那间就下了决心要自立门户。
面对这年幼的少女,他突然不再眷恋自己那张呕心沥血的美人图了,就连原本被他奉为灵感之神的兰花,都被置之脑后。
当晚他就收拾行李,离开了皇甫珍为他准备的安乐窝,跟他一起回到西京的,还有来路不明、苍白消瘦的幽兰。
曲宣并不知道,自己所有的举动都落入了某双清冷如水的眼眸中。
“老头子,你就这样看他们私奔吗?”阿朱陪在老头子身边,两人坐在高高的树上,将这落魄画师的哭泣和奔走都看在眼里。
“志同道合的人,早晚会在一起,我又怎能阻止?”老头子打了个哈欠,今晚他喝得有点多,稍显疲惫。
“可是那小姑娘不是说要杀‘妒鬼’么?你就放任她胡闹,不把她留在身边?”阿朱不以为然地说,“她会不会是为了得到你的血在撒谎?”
“谁知道呢,妖怪的心我永远都猜不透。不过我相信幽兰。”老头子轻抚着阿朱如绸缎般华美的黑发,“她压抑得太久,必将一鸣惊人,就像那个男人一样……”
阿朱伏在他的怀中,并未反驳。月亮的影子越发圆满,似乎转眼间,盛夏就如奔马般呼啸而至。
西京城中百花盛开,迎来了一年中最繁盛美丽的时期。
但自立门户远没有曲宣想的那么简单,失去皇甫珍的庇佑,他活得很是潦倒,背着画具在西京风餐露宿,连找了三天,才找到一间据说是闹鬼的茅屋住下。
室内尘灰满地,狭窄得一下床就到了房门口,跟这陋室比起来,皇甫珍为他提供的遍布奇花异草的庄园简直堪称宫殿。
所幸幽兰并没有抱怨,她像是一只出笼的小鸟般欢快,力所能及地布置起了这个简陋的房间。
只是每逢夜深人静,曲宣总是能看到她坐在院子里,望着涤荡的夜风发呆。时而会有白色的飞蛾落在她的指间,她就会对这只能在夜间活动的昆虫说几句话,再挥手放它们离开。
而当夜蛾振翅高飞时,曲宣总觉得这个消瘦的女孩也会乘风飞去一般。
日子流水般滑过,曲宣每天都去集市卖画,只是现在他笔下的美人已经不再丰腴美丽,眼角眉梢,都带着贫苦孤寂之色。
再也没有什么珍稀花朵供他想象了,这都是他对着绿柳画出来的作品,难免也沾染了尘土之气。
没有书画店的老板肯让他进门,更没有人愿意给他的画出个好价钱。他只能跟小贩一起站在街头叫卖,每日卖画所得不过十几个铜钱,跟皇甫珍当初给他开的价码一样。
他布袍上沾满油彩,简直快看不出本来的颜色了,而在西京的闹市中,他也曾见过皇甫珍在众人的簇拥中高歌而去。
但这位风流俊逸的才子却不曾对他和他的画瞧上一眼,或许画上平庸的手笔,已经让他泯灭于众人,毫不惊艳了。
“卖了那幅洛神图吧。”在一个凉爽的夜晚,当曲宣带着可怜的画资回到家时,幽兰轻轻地对他说。
半个多月下来,她更瘦了,身上的白衣也变得黯淡无光,只有一双大眼睛仍然炯炯有神,恍如暗夜中跳动的烛火。
“可是我恐怕再也不能画出那么好的画了。”曲宣垂下了头,这些艰难的日子磨去了他的才气,那些依照鲜花画美人的逍遥日子,明艳得像前世的记忆。
“再这样下去,你就什么都画不出来了,你甘心吗?”幽兰咬了咬薄唇,大眼睛中含着不屈的光芒,“难道你想一辈子做一只见不得光的蛾子,在黑暗的角落自生自灭?”
蛾子?
像是洪钟敲醒了沉睡的人,曲宣抬起头,他想到了那种恶心丑陋的昆虫,只能在夜间出现,永远不被注意,即便投火而死,也只落得个愚蠢的名头。
“不……”
他几乎是咬牙切齿地说,眼睛里像是藏着一簇跳跃的火焰。
四
七月十五,中元节。
家家户户都忙着祭祀先人,不少人家举家出动,去西京的郊外扫墓祭祀祖先。还有的人家留在城中,晚上去洛河边放花灯祈福。
这晚月朗星稀,明月像是个完美无瑕的银盘,将尘世照得如同白昼。既照亮了西京城千顷华厦,也照出了一个佳人窈窕多姿的影子。
那是个身穿素衣,从西京的下城中走出来的女子,她鬓上别着一朵白花,似乎新寡。可是看她那妩媚的眼角流露出的风情,又毫无悲戚之色,尤其眼角的一颗黑亮小痣,宛如黑宝石般衬托得她的眸光更明丽似水。
“就是这个女人,每天都招摇过市,专门挑晚上出门,简直比花楼里的花娘行首还忙。”一棵高大的槐树上,阿朱正对老头子耳语,“我已经跟了她几天,如果‘妒鬼’再次出手,目标十有八九就是她。”
老头子望着女人纤细的腰肢,她像是弱柳扶风般在夜色中走着,每走一步,都勾画出优美婀娜的曲线。
“或许,就是今天呢。”他目送着女人远去,以轻不可闻的声音说。七月十五,月满如盘,百鬼夜行,还有什么日子比今晚更适合杀人呢?
女人优雅而颇具风情地走到了洛河边,河上游挤满了放河灯的百姓,她十分嫌弃地皱了皱挺秀的鼻子,眼角的小痣微微一跳,似乎不喜欢与众人拥挤在一起。
她索性提着竹篮,分花拂柳地向寂静的河下游走去,既避过人群的喧嚣,又躲开了几个登徒子孟浪放肆的目光。
“千万恨,恨极在天涯。山岳不知心里事,水风空落眼前花……”她点燃一盏荷花灯,一边将花灯放在水中,一边唱着温庭筠的小调。
烛光映着水色,照亮了她皎洁的侧脸,眼角的小痣宛如泪珠,挂在颊边。此情此景,像是浸润了千百年来人类生离死别的惆怅,离人不归,歌声不歇。当岁月如怒海惊涛般奔涌而去,当初等待的人早已化为白骨,只剩下这凄婉歌声,在时光中空自徘徊。
隐身在河堤长草中的老头子,也被她的悲伤感染,发出了一声低低的叹息。一直心无挂碍的他,罕有地生出了要保这女人平安的念头。
因为这首饱含深情的小调,她在他眼中不再只是个“饵”,而是变得生动明丽起来。
就在这时,不知从哪里刮来一阵腥风,熄灭了河灯中的白烛,河边只余下了星月辉光。女人惊恐地环顾四周,但还没等她看清,就有一个强壮的身影从河底跃出来,一把掐住了她的脖子。
那人周身覆满坚硬的青色鳞片,根本看不出本来面目,活脱脱是个从画中走出来的恶鬼。
“天下的漂亮女人,都要去死!”怪物低吼着,手上加力,眼看这小寡妇就要命丧在他手中。
老头子朝风中打了个响指,一阵旋风平地而起,眠狼尚未现身,宝剑已然出鞘,一剑就刺中了怪物的手腕。
怪物一惊,看清眠狼冷峻的脸后,察觉到有人伏击,急忙撒腿就跑。
“别让他跑了,这人跟妖怪同化了,一定是有人教给了他什么法子。”老头子心中默念,他与眠狼心意相通,英俊的黑衣少年立刻明白了他的想法,将长剑舞得滴水不漏,完全封住了那人的去路。
但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那怪物居然双手抱头,大喝一声,直朝眠狼的剑尖撞去。眠狼想要收剑已经来不及,利剑刺破他周身覆盖的青色鳞甲,迸发出闪亮刺眼的火花,怪物飞快地荡到了一边。
“阿朱!”老头子急忙跳出草丛,刚要召唤阿朱,有一个人却比他更快。
只见那一直沉浸在悲伤中的女人突然一扬手,一道白光脱手而出,追星赶月般直刺向那怪物的后心。
浓黑的夜色中传来一声闷哼,怪物在河堤上奔逃,几个起落就逃离了他们的视线。
阿朱倒悬在一棵柳树上,她朝老头子使了个眼色,锲而不舍地追上了那抹消失的影子。
“都怪你多管闲事,不然我早就杀了他。”方才还惊惶万分的女人将长发打散,玉手翻飞,将发髻梳成了少女的长辫。
她的竹篮翻倒在地,篮中的河灯下竟然放了十几把匕首,刀刃上画满了扭曲如虬蛇的红色咒符,触目惊心。
“这不是我见到的第一个能驱使妖怪的人类,背后必定有人在暗处捣鬼。你为什么要杀他?”老头子并不生气,只偏着头望着她。
她小巧莹白的脸,那眼角的黑痣,都像是个谜,等待他破解。
“不为什么。我早就想杀掉‘妒鬼’,惩恶扬善。”少女白了他一眼,收拾好竹篮就要离开,脚步匆匆,似乎在逃避什么。
“你以自己为饵,孤身一人行动,冒这么大的风险,怎么看也不像是出于正义啊?”老头子像是想到了什么,笑容浮上了他年轻俊秀的脸庞,使他看起来就像个风流公子,“你,该不会就是之前那个恶作剧的‘妒鬼’吧?”
少女停住了脚步,恶狠狠地回过头,瞪着这个聪明的少年。眼角的一点黑痣随着她愤怒的表情跳动,像是一颗蓬勃而发的芳心。
在同一个夜晚,喝得醉醺醺的皇甫珍走在回家的路上。最近他心事颇多,供养的画师跑了,没人再替他画美人图换钱,而且千福寺请他画《地狱变》的住持,居然对他颇有微词。
“公子年轻,似乎不了解什么是地狱呢。”老住持只看了一眼他的画,就笑眯眯地摇头,“没见过地狱的人,是无法画出真正的《地狱变》的。”
“难道吴道子见过地狱吗?混蛋,他懂什么!”想到被人折辱,他就忍不住咒骂。
然而暗巷中猛然蹿出了一个人,似乎体力不支,一头就扑到了他的怀中,他的手中立刻沾满了黏腻温热的液体。
他吓得连忙看向自己的手掌,指间的液体像极了鲜血,但那血却是绿色的,就像他用花青和藤黄调出来的那种草绿。
他吓得惊慌失措,一把推开男人,在西京的街道上狂奔。可是那绿色的血液却怎么也擦不去,像是与生俱来的胎记般,牢牢印在他的皮肤上。
待续
出自《龙文·漫小说》VOL.11
多多80后青春幻想文学作家。现居北京,曾用笔名『可爱多的粉丝』。喜欢美食,喜欢操纵金融的感觉,喜欢听细腻的对白。代表作《春江花月夜》系列、《百鬼》系列、《不可思议事件簿》系列、《锦瑟》、《死神来了》、《以S之名》系列、《灵魂摆渡》系列、《长夜幻歌》系列等。?点击下方的填写电子调查表,将有机会获得编辑部送出的神秘礼物哦!
微博:
龙文漫小说贴吧:龙文漫小说吧
赞赏
转载请注明:http://www.dongyamedia.com/zzyz/8986.html